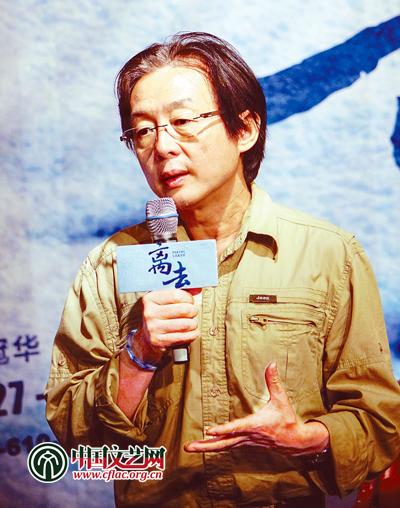
王曉鷹執導的新戲《離去》6月27日在京首演
“他不是一個病人,他是一個嶄新的人。”三女兒考狄利婭仿佛就在一瞬間,突然理解了患阿爾茨海默癥的父親艾略特·布萊恩,這個一度叛逆不羈的女孩眼睛里全是淚水,站在客廳里和兩個姐姐對峙,她的二姐,堅持要把房子賣了送父親到養老院去,賣了房則無處容身的大姐因為這個計劃憤怒和絕望。此時,她們的父親,在舞臺上演了一輩子李爾王的艾略特·布萊恩半躺在沙發上,目光空洞,背后是一個放滿了莎士比亞劇作的書架。由國家話劇院打造的話劇《離去》改編自美國當代劇作家奈戈·杰克遜的劇作Taking Leave,由著名話劇導演王曉鷹執導,將于6月27日至7月6日登陸國話劇場。
舞臺上設置了一個樓梯,演員章劼飾演艾略特·布萊恩的“影子”,代表的是他清醒的自我意識,最終“影子”走上樓梯隱入黑暗之中。“離去”即清醒的自我意識離主人公艾略特·布萊恩而去。這是一個患病的父親跟三個女兒之間的故事,王曉鷹說,這部戲并不是從醫學或者社會學角度探討阿爾茨海默癥本身,也不是討論親人們應該怎么對待這樣的病人。“主人公的經歷和痛苦,他跟影子之間的對話,這樣的生命狀態最后呈現出一種藝術力量。”
記者:這部戲里,“影子”這個角色的設置很有新意,也成為該劇的一大亮點。
王曉鷹:這個“影子”是原劇本就有的,我們修改了下劇本,現在相比之下影子的戲少一些,艾略特·布萊恩的戲多一點。艾略特·布萊恩是一個阿爾茨海默癥患者,他已經很難是正常狀態了,在整部劇中他沒有把三個女兒清晰地認出來過,他跟三女兒那么動人的一場讀《李爾王》劇本的戲,但從頭到尾他一直是以李爾王的名義,把他的三女兒當做劇中的考狄利婭,就像當年特意給女兒取這個名字一樣。大女兒、二女兒他有時候還能認出來,但沒有一瞬間是把三女兒認出來的。這個戲并不是講阿爾茨海默癥面對的外部世界:他怎么面對家人,孩子們怎么面對他,它其實更多地講的是艾略特·布萊恩內心的痛苦、糾結、掙扎,從一個正常思維漸漸進入迷亂思維的過程當中,他的那種恐懼感,這正是靠影子的表達以及他跟影子之間的對話來呈現的。那個影子其實就是他清醒的自我意識,是他對外界和自我的理性判斷。
記者:你要求飾演影子的演員章劼怎么來演?
王曉鷹:章劼一開始覺得這個人物沒有內容,比較理性,但演起來時,我要求他把臺詞說到位,意思說準確、清晰,有時候還要說強烈。他慢慢意識到他說的是艾略特·布萊恩的內心感受,你得有他的內心感受才能說得出來,包括他自己的感受,對孩子們的內心感受。這個戲有好幾個層次,包括艾略特·布萊恩這個人物也如此,所以王衛國演這個戲很過癮,他要演這個人物的四層。最直接的一層,他得了阿爾茨海默癥以后的那種混亂狀態;第二層是他正常情況下會跟身邊的人有怎么樣的交流;第三層是他跟影子一塊兒演戲的時候,要表達他的內心感受和痛苦;還有一層是演李爾王,他在舞臺上有大段的以李爾王名義演的戲。
記者:有一場戲,他跟三女兒考狄利婭一起讀《李爾王》劇本,很令人動容。
王曉鷹:這是一段特別動人的戲,三女兒給他讀李爾王瘋了以后那段臺詞,他一聽劇本,在病情很重的情況下,還是很準確地接上了李爾王的臺詞,慢慢發展成他跟三女兒基本上以演的狀態把那段戲呈現了出來,最后兩個人蹲在地上,對話非常投入感情。這一段戲,觀眾分不清楚這時究竟是劇中的考狄利婭跟李爾王在對話,還是三女兒在跟艾略特·布萊恩在對話,整個臺詞和人物情感全部融合到一起了。
記者:這部戲跟原劇作最大的不同,是把艾略特·布萊恩從一個研究了一輩子莎士比亞戲劇的大學教授,改成演了一輩子莎士比亞戲劇的演員。為什么會做這樣的改編?
王曉鷹:1998年我在美國看了這部戲的演出,想把它拿到中國來演,是出于兩個原因,一個是它的內容很特別,我們當時還不知道阿爾茨海默癥這個術語,而叫它老年癡呆,以這樣一個方式寫一個人特別的內心感受,特別的生命掙扎,國內還沒有。我喜歡那種非同一般的、不是日常生活中大家都能夠很容易體驗的人生經歷。再一個是它的表達方式,劇中設置了一個角色艾略特·布萊恩1,后來我們改成了“影子”,用這兩個角色的關系表現主人公的內心感受,我覺得這種形式也很特別。
我回來就找人翻譯劇本,第二年就翻譯出來了,但后來一直沒排,因為我只是覺得它挺好,但我自己的創作沖動沒找到。一直到有一天我想到,應該把他改成一個演員,就忽然一下覺得有排的動力了,這是兩年多前的事兒。
記者:為什么選王衛國來演艾略特·布萊恩?
王曉鷹:當我想到要把他改成一個演員的時候,腦子里幾乎同時就想到了王衛國,要是這個角色是一位學者,肯定不這么選。王衛國適合演李爾王這個角色,同時,一個這么高高壯壯的、聲音這么好的人,演這種生命的枯萎,這種無助、焦慮和恐懼,可能更有打動人的力量,所以就選了他。
記者:演員對阿爾茨海默癥的把握和演繹,會不會比較難。
王曉鷹:得阿爾茨海默癥的人,沒有一個人從那條路上回來過,你沒法知道走上這條路的過程中,他心里的痛苦、恐懼或者是別的什么感受,以及到了什么程度,他對外界感知到的到底是多少。比如有時候躺著的植物人,其實我們說話他聽得著,那也是我們的推斷,不太可能知道他內心感受到底什么樣,如果他斷絕了對外界的感知后,內心到底是個什么狀態。我們演這個戲為什么難?因為演員不知道的話是演不了的,演員就是要演一個特別的生命階段,演這個人物這個時候的掙扎、痛苦、恐懼。有的時候,我們需要找到一種,我們理解的他跟外界錯位的那種機制,找到他清醒的時候、病的時候不同狀態下的轉換,把他跟真實狀態之間又模糊又復雜的聯系建立起來。這個東西是我們不太可能用自己的生命感受和認知去建立的,就要靠我們做戲劇創作這么多年和演員這么多年練就的一種能力,你去用自己的想象和體會去演,但是要準確,這點上比較難。
記者:你在向國內觀眾介紹外國戲的時候,選擇戲的標準是什么?哪些元素是你要考量的?
王曉鷹:我把外國戲介紹進來,不管是經典劇目,還是像《哥本哈根》《離去》這樣的新經典,不一定考慮它的觀眾接受度,更不直接考慮票房,我考慮的是如果從國外引進戲來,它給我們劇院、舞臺、觀眾、戲劇界,能夠輸入多少我們之前沒有的新東西,包括內容上的開掘,對人的開掘,我們之前沒有過這種角色,或者沒有這種深度的角色,它的戲劇的表達方式,對我們來說應該是有啟發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