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為山
吳為山先生是具有廣泛國際影響力的雕塑家,由他提出并踐行的“寫意雕塑”廣為世人所知。雖以雕塑名世,但吳為山成就卻遠不止于雕塑。就理論研究而言,他的藝術觀念、美學理論、教育理念、傳播意識和文化觀點均值得細品。事實上,吳為山是一位跨界者。他身兼美術學、設計學、宗教學三個方向的博士生導師,在美學、美術學、設計學、宗教藝術、審美心理學、審美教育學、博物館學、文化傳播學等方面皆有豐厚成果。他主編了《西漢木雕》《長治彩塑藝術研究》《中國雕塑新銳》《雕塑文論》《中國佛教文化藝術》《中國佛教藝術》《吳哥雕塑藝術研究》等多部論著;撰寫了《中國古代雕塑風格論》《視覺藝術心理》《雕塑的詩性》《雕琢者說》《吳為山藝文集》等數十部學術專著、論文集和學術隨筆;還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重要媒體以及《文藝研究》《美術研究》《美術》等重要學術期刊發表《中國古代雕塑的八大風格特質》《雕塑與人文精神》《寫意精神與雕塑》《以美育提升人文素養筑牢文化自信》《文化生命的孕育》等各類學術論文數百篇。其中,多篇被《新華文摘》《人大復印報刊資料》等極具權威性、學術性和品牌影響力的人文社科類數據庫轉載。可見,吳為山所跨的每一個“界”,皆能專而至精,它們非但沒有變成前進的掣肘,反而成為催生新思想的重要助緣。
這與吳為山的人生經歷不無關系。受家學熏染,他自幼熟習書法,青年時代接觸雕塑,大學時專擅油畫,畢業后留校任教而轉向教育理論研究并赴北京大學進修心理學,繼而又負笈歐美,先后到歐洲陶藝工作中心、華盛頓大學美術學院訪學交流。“轉益多師無別語,心胸萬古拓須開”,吳為山憑借豐富的閱歷而開闊了視野、打開了格局并提升了境界。更重要的是,雖然不斷涉及新領域,但他從未放棄既有領域,而是讓不同領域在此過程中相互激蕩、相互啟發、相互滋養,共同成就了其精彩的跨界人生。也因此,當吳為山進行理論研究時,提出的觀點往往能跳出專業分類的局限而獨有千秋,值得反復揣摩玩味。換言之,閱讀其文章、著作,往往總能讓讀者的審美期待得到極大的拓展。日前,由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美在中國美術館:吳為山論展談藝錄》(以下簡稱《美在中國美術館》),相信可以使讀者擁有這樣的閱讀體驗。
《美在中國美術館》分為五個板塊:中國古代美術、近現代美術、當代中國美術、現當代外國美術和綜合類,它們是作者近幾年為中國美術館部分重要展覽所寫的序言或發言稿。這些文章長短不一,以辨名述理為主,中國畫、油畫、版畫、雕塑、工藝美術、攝影、素描等藝術類型皆有涉獵;專題展、個人展、捐贈展、文獻展、交流展等不同展覽類型盡收筆下。有宏大敘事,也有個案研究,徜徉恣肆,要言不煩,再配上精美的插圖,猶如一個既有“大菜”“硬菜”也有精美“點心”的學術“拼盤”。這些文章不僅是理論研究,同時也是藝術評論,視點多維度,觀點多洞見,論述無套路,思維有交叉,字里行間顯現出其有態度、有溫度、有角度且有意思的藝術靈魂。下面,筆者選擇幾個話題對這本書進行簡要介紹。
1、展覽中的傳統與道統
《文心雕龍·隱秀》篇中說:“文之英蕤,有秀有隱。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讀者直接看到的內容,固然是作者和編者才情嘉會之成果,屬于獨拔之“秀”者,但伏采潛發,秘響旁通方為文外之“隱”意,才是作者更想讓讀者領悟體察的要義。要讀出《美在中國美術館》文字背后的“隱”,必須將它們放進中國美術館展覽這一特定語境中。其實,書名本身便已透露玄機,加之書中每篇文章后面,都附有相對應的展覽介紹,說明編者從一開始便有意識地想提醒讀者,這些文章的誕生和傳播本處于中國美術館展覽這一原初語境之中。只有將它們納入此原初語境,才能感知到作者眼光和胸襟的非凡之處。
眾所周知,美術館是收藏美術史、呈現美術史、書寫美術史的地方,很多人至今也認為,當作品被高級別的美術館收藏,就意味著與美術史發生了直接關聯。基于此,美術館策展也相應地將以“史”為主線作為基本學術立場和策展理念對藏品不斷歸納、總結、研究、發現。美術館很多常設展或館藏展都圍繞著藏品開展,用史學邏輯或社會歷史觀進行學術脈絡梳理。而美術館的展覽敘事也一直與美術史保持著互動關系。一方面,美術史的研究成果會影響美術館的收藏與展陳;另一方面,美術館的展覽敘事的某些觀念和形式也會對美術史學研究產生影響,甚至還會形成對已有美術史的補充甚至再書寫。因此,美術館展覽就是一種美術史現象,屬于美術史的一部分。而這本書的結構編排,很大程度上也體現了“史”的邏輯,故而其內容天然地帶有美術館的展覽敘事性。吳為山正是以策展人尤其是中國美術館總策展人的身份與眼光,重新審視了中外美術史,并按照自己的理解進行研究。說到這里,則又應該回到作者跨界身份的豐富性和文章表達語境的特殊性上來。作為國家美術館的館長,吳為山在中國美術館的展覽中表達的觀點除了代表自己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國家當代文化的立場。比如,在《東吳萬里墨韻流芳——600年吳門畫派文脈與復興》一文中的觀點,就非常典型地體現了這種源于作者身份和表達語境的影響。吳為山將明清至今的600年吳門繪畫總結出四個特點:兼容并蓄、多方融合、含蓄蘊藉、以道統藝。其中的第四個特點,格外彰顯了作者的站位與獨到。因為如果單從學界視角看,明清的畫學道統觀對山水畫的多樣性發展實際上起到了阻礙作用。如“四王”一派的“師古”始終局限于固定的幾個人,放棄了更多營養攝入的可能,導致作品面貌單一,程式僵化。若以史為鑒,確立畫學道統似乎并無珠玉在前。然而,吳為山卻從其中能看到道統之于畫學的正面價值和積極意義,提出:確立道統,以道統藝,讓母題限定和價值范式發揮其最大作用,幫助創作者審視、矯正創作主體的絕對自由所可能帶來的虛無和偏激。
顯然,吳為山絕非不知道明清畫學道統所產生的弊端,但他能跳出時空偏狹導致的陳見,看到了道統意識在讓個體接通時代脈動、融入文化傳統中發揮的重要作用。近百年來,中國美術一直受到來自西方的深刻影響,甚至一度在其身后亦步亦趨。中國文化藝術的短板在這百年間也得到了充分的剖析與批判,不過批判不代表否定,更不能代替建構。如今,中華民族正走在偉大復興之路上,這條復興之路本身也是一段尋根之旅和重建自信的過程。批判傳統固然有可貴之處,但此時對傳統的認同,于民族偉大復興而言則更有現實意義。傳統不是塵封的過往,不是靜止不變被定型的存在,它包含過去、呈現當下、開啟未來,是不可分割的綿延之流。我們不能規定傳統,而要與時俱進,要使之永遠處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中。因此,吳為山審視傳統,落腳點在未來而非過去。他站在未來的角度回溯歷史,從中發掘更多的可能性源泉,強調對傳統進行重建。在此基礎上,吳為山提出了“在當代中國現代化進程和新文化建設中重構畫學道統”“使個體的藝術創作在道統性的彰顯中超越自身意義,獲得升華,邁向不朽”的要求和希冀。正因為如此,我們看到吳為山對整個美術史都充滿著一種包容與溫情,他更希望發掘畫家、畫派乃至畫史中積極向上的因素并將其呈現——這是一種姿態,更是一種心態和一種狀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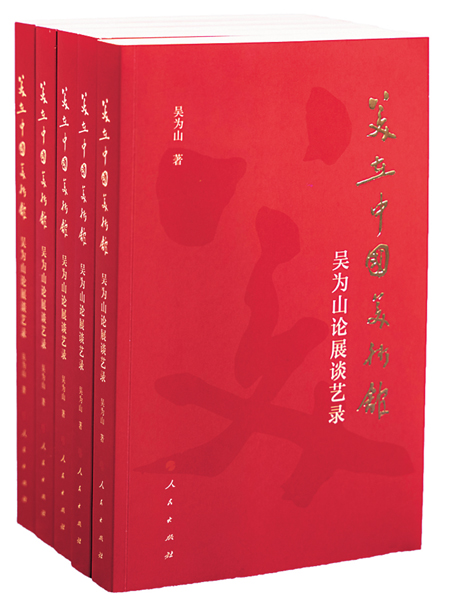
吳為山專著
2、大師與美術史
吳為山對待傳統的思維方式是整體性、有機性的,因此能根據不同語境、不同目的而不斷刷新視角,真正做到用現在和未來賦予和決定傳統。《美在中國美術館》一書中,收錄了他為幾位近現代中國畫大師的展覽所寫的長篇序言,筆酣墨飽,斐然成章。如在《黃賓虹:渾厚華滋我民族》中,吳為山拋出了一個“靈魂詰問”:“為何認識和解讀一位真正的藝術大師如此艱難?”繼而,他從黃賓虹對其身后美術史的影響入手進行分析解答,選擇黃賓虹的兩位最具典型意義的弟子林散之、李可染為代表,有意識地區分了書法和繪畫兩個領域,不僅生動地體現了一代藝術宗師如百川匯海與千江之源般的雍穆氣度,同時也突出了文脈的流傳演進必須要在創新中實現這一要義。再如《傅抱石:搜盡奇峰寫性靈》一文中,吳為山提出:要了解美術史,最直接的方法便是研究具有典范意義的大師——從作品的圖式到內容,從時代背景到地域文化,從藝術家的個性特征到民族文化的集體積淀……由此,我們才會在一個廣闊而深遠的文化時空來審視藝術現象,進而在比較中獲知藝術生態的流變。吳為山在此明確指出自己的美術史研究方法論,其中“最直接”三個字,傳達出一種不容置疑的自信,恰恰暗示出只有成為“具有典范意義的大師”,才是真正值得敞開心靈與之對話的,充分反映了他能夠平視歷史、對標先賢的眼光、格局與境界。在這篇文章中,吳為山還藉由總結傅抱石的畫風,提出了“筆墨當隨時代、筆墨當隨地域、筆墨當隨性情、筆墨當隨心象”,既發展了清代石濤“筆墨當隨時代”的美學命題,某種意義上也是針對中國畫文脈的當代傳承而構建出完整的審美創作體系框架。
除了運用整體性、有機性的思維方式審視傳統外,吳為山還運用一種對比互動的思維方式觀照美術現象。這是一種充滿辯證張力的思維方式,面對來自西方、來自時代、來自意識形態的要求,他深刻反思當下中國美術在認知和實踐之間可能出現的斷裂、當下和傳統之間可能產生的沖突,以及本土文化和外來文化之間可能發生的對立,繼而進行自主選擇與主動融合,提出見解,做出判斷。如在《雨后青山鐵鑄成——談潘天壽》一文中,吳為山同樣是立足于未來,確定了潘天壽的美術史坐標。一般來說,學界是將潘天壽視為中國畫最后一位集傳統之大成的大師,歷史定位和評價亦都以此為基調。而吳為山卻能前瞻性地認為,潘天壽之于美術史的真正價值與意義乃是:走進通往現代的大門,用匹配時代的陳述方式完成了從古典向現代的轉化……在新的歷史語境中為我們回歸精神家園指明方向。
可見,他更加看重潘天壽對中國畫傳統的突破與轉化,強調其“在集大成的基礎上摧陷廓清,創造出體現生命意志的心靈圖式”,從而凸顯中國畫超越時代之上的文化屬性、自然屬性和歷史屬性。事實上,吳為山所觀照的美術史,總能突顯不同的歷史氛境,以設身處地的時代聯想透析藝術創作與社會背景,體會藝術家的命運軌跡與理想追求,從而看到一條反映美術與時代同行并不斷積累和延伸的成長之路,由此豐富和深化認識中國美術發展歷程的文化價值。

2017年11月17日至26日,由中國美術館策劃并主辦的“美在新時代——慶祝‘十九大’勝利召開中國美術館典藏精品特展”在中國美術館面向公眾開放。展覽迅速獲得觀眾叫好,超出日常參觀量的5倍之多,排隊觀展的隊伍綿延長達2公里,與11月北京凜冽的寒冬相比,場面可謂異常火爆。
3、筆墨與人格境界
吳為山對美術本體的認知尤能切中肯綮,分析亦剔膚見骨。比如,他在解讀傅抱石的“線”時,深入道家哲學,從有與無、動與靜的辯證性存在中尋找其文化根據。他將“線”與“面”對舉,指出“塊面是一種實實在在的靜態‘存在者’,線條則是趨向于‘無’的動態‘生成者’”。基于上述分析,傅抱石的“抱石皴”被創造性地理解為一種“從有復歸于無而來”的“線”。我們知道,“抱石皴”是傅抱石最具辨識度的技法,歷來為畫界、學界所熟識。而吳為山卻能別具慧眼,看到其“僅少之形,因附色于‘無’成象而展開”的造型特點,體會其“亦真亦幻,亦動亦靜”的審美特質,發現其“超拔沉淪之存在,遠離現實之況味”的哲學意蘊,恰與老子描述“無”含于“有”的恍惚狀態相通,是一種尤其能體現“道”之悠遠深邃的視覺形式。所以,把它總結為“既是自觀自聽,自視自照的映現,亦為中國古典藝術精神之‘聰明’‘老境’的彰顯”。并且,吳為山還透過“線”這一獨特視角,充分詮釋了“線”作為中國書畫之本體的美學特征:(傅抱石)常常是為“線”而尋覓題材,不同的對象對應不同的審美意象。以凌空楊枝的疏朗表現線的“沖淡”與“逸動”;以穿越的過山索道表現線的勁健和韌性;以井架的高壓電纜表現線的綿延和秩序……
同時,吳為山也深刻地指出“線”之所以成為傅抱石藝術的核心,乃是:由于書法篆刻而體現的功深百煉的底氣,還折射著他以線性而神合心性的自在與悠游。這是由技而道的藝術體驗,是一線終古接天涯的圖像表征。在此,吳為山極深研幾,將藝術家的審美旨趣和繪畫風格追溯到造化之始、生命之初的哲學本源處,尋找藝術家本真心性與乾坤規律的契合點,揭示中國繪畫的筆墨本體與大道運行的同構性,探賾索隱而得之人所未得,闡幽發微而見之人所未見。以至于抱石先生的哲嗣傅二石看到后,特地撰文在《光明日報》刊發,稱“傅抱石的獨特之處,超人之處,幾乎都被文章涉及了”。傅二石還特別提到,吳為山對“線”的認識,“深到超出許多人的理解力”。
吳為山不僅考察美術本體與客觀物象、現實世界乃至宇宙本體的關系,同時也極為強調其與心性修養以及人格境界的關系。在中國美學體系中,人品往往呈現于作品且人品不能靠技法習得。故而,中國藝術的最終落腳點絕不是創作出作品,而是創作者人格境界的提升。換言之,就中國藝術而言,真正的本體其實是人。誠如清代張庚所說:“德成而上,藝成而下”。這種獨樹一幟的理念,正是中國傳統藝術精神之所在。吳為山對個中道趣深切著明,因此他在研究具體藝術家時往往格外看重修養心性的工夫,即突出藝術家通過涵泳經史、臨習前賢等方式,存養擴充自己的胸次襟度,形成高遠人格境界的過程。如《昂揚與儒雅的風骨——談高二適書法的人格氣象》,吳為山在文中提出一個概念—— “人格氣象”,并將高二適書法的“人格氣象”分為“書卷氣”“才氣”“骨氣”三個重要因素。
所謂“書卷氣”,本質是“民族文化的積淀”,必須“洞明文字生成中所蘊自然山川之地脈、宇宙變幻之天象,深諳文字之文化含量”,使之“生發出意象、意念、意蘊、意境”。吳為山還以自身極為敏銳的審美感受力,發現高二適書法與詩歌之間的通感性所展示出的“書卷氣”:神交諸體流變,暢通主體之情,虛渾圓融,自成一體。其陰、陽、頓、挫,以及飛動的線條和鏗鏘的運筆,在文化的時空唱和于杜子美、李謫仙、白樂天……
所謂“才氣”,其體現于“創造性”。而“創造性”又體現為創作者“以文化之,深諳諸體與百家,且信手拈來,于自然揮寫之瞬間得眾美之妙,仿佛深藏之甘泉瀕瀕溢出”。進而,吳為山指出高二適書法的“才氣”與其“書卷氣”之間的關系:憑藉吟哦所養之氣,功深百煉之力,自信點劃,一線橫空,全仗性情所致,將書法的疏密節律對應于一瞬靈感,故幅幅皆殊,各美其美,予書法審美以多維空間。
所謂“骨氣”,是指“不求功名”“只為真理”。古人早有“骨法用筆”的審美標準,歷史上也一直高標用筆的線條應有力量感。但古人所說的“骨法”并未與人格道德直接關聯,而吳為山則明確賦予此用筆中所蘊涵的力量應是一種人格境界的折射和道德力量的彰顯。他認為,高二適的“骨氣”正是“不畏權勢”和“堅持自己的學術觀點”,當它外化為書法時則“為狼毫用筆,信筆直取,力度遒勁”,在“昂揚、激蕩的書法筆鋒里折射著古人的高古,文人的高雅”。
本書中很多文章都是基于畫家的人格境界來審視其藝術境界。如《為萬世開太平——于右任書法作品展》,吳為山將于右任的書法看作是:將一生戎馬文心、赤肝忠膽注于筆端,得正大、雄邁、磊落、渾樸之氣象。方之書史,唯顏魯公與其似之。還有前文已經提到的《雨后青山鐵鑄成——談潘天壽》,吳為山認為畫家的書畫藝術整體上反映出一種“楷書的靜態造型美學”“其中剛毅之道德意味和執著之生命情態恰與儒家的人格精神同構”。潘天壽“沿著盡心、知性、知天一路走過,將胸中的浩然之氣充塞于自己的藝術世界”“直通于天地之間的凜然生命力”,與其“壯美”的視覺風格一起“共同育成了人格符號的價值取向”。
綜上可見,在吳為山眼中,真正偉大的藝術必須要有偉大的人格為依托,心性修養是途徑,人生境界則是基礎。這一觀點強調創作者要在關注藝術本體的同時,不忘透發出一種正大光明之概,充分闡釋了“道”與“人”之統一的原理,實乃對偉大的中國傳統藝術精神的傳承。
吳為山手書的“寫在美在中國美術館一書出版之際”墨跡
4、理論的文學性表達
理論研究通常是基于一種對象化的剖析思路展開,研究對象之于研究者而言,乃是外在的、可以被客觀描述的存在,因此理論研究往往顯得“灰色”。而一些專門從事理論研究者,又往往會脫離美術現象本身而停留在邏輯推演層面,用旁征博引或故弄玄虛的概念制造來掩蓋對事實本身理解的蒼白。某種意義上,這類文章成為作者設問自答、自圓其說的文字游戲,要么觀念先行、要么結論費解。而《美在中國美術館》卻是一部活色生香的理論性作品。畢竟,吳為山諸多身份中最讓世人熟知的,還是一位成就卓越的藝術家。他即使在寫理論文章時,文字也從不缺乏感性與靈動,具有獨特的面貌。讀者完全可以從他酣暢的行文中,感受到一種與生俱來的敏銳感受力和精準直覺。如《以文字景仰吳冠中先生》的行文:春天,人間的四月天,桃紅、嫩綠,健枝舞動,柳絲綿綿,誰家飛燕入夢?青山一抹,湖面如鏡,點點白鵝,劃破江南的寧靜,這油彩的芳香,筆筆含情……寥寥數語,吳冠中作品的神韻便如在眼前。尤其一個“抹”字,堪稱神來之筆,飄逸、輕盈,生意盎然,江南意境和盤托出,讀來令人頰齒留香,心弦也在不經意中被輕輕撥動。
再如《大美至樸——羅爾純藝術展》中,他寫道:“紅得令人心醉的土地,在凝重、淳厚的飽和色漿中翻動著富有激情的筆觸,層層復加而又層層留底;扭曲升騰的大樹直入翻卷的云天,放牧的農家女消融于紅土地,而燦爛一片。同樣默默向著天方歸去的耕牛,在這紅調子中更顯得自在。”這些描述文字仿佛夢囈卻又真實準確,一下子就捕捉到了最具辨識性且最富感染力的畫面特征。它們叩擊感覺、喚醒體驗,凡對描述對象有過視覺經驗的讀者,一定會引起深刻的共鳴,而未曾見過描述對象的,也定會心生向往。
不僅是描述,點評亦動中窾要。如《夢游詩園——皮埃爾卡隆油畫藝術展序》中說:“和西方古典美術告別后,塞尚及其之后諸多藝術流派的抽象表現,似乎可以找到主觀世界的對應。但人類的認識和審美,視覺經驗和形式創造,總是在主客觀間求得平衡,藝術方能進入心靈,成為精神的慰藉。因此西方藝術在經過平靜與動蕩、保守與革命之后,開始回眸那遠古的、原始的藝術。生生不息的自然是先民樸素的創造之源,文明時代則追尋那‘詩意地棲息’。”這真是香象渡河之語,完全沒有被政治體制、思想演進、藝術生產等看似時髦卻老生常談的研究套路所遮蔽,且跳脫出文化和國別的差異,直接從心物關系的哲思出發透析美術乃至文明的演進邏輯。若非悟道精深,絕不可能寫出此等文字。
吳為山對作品風格來源的判斷,同樣鞭辟入里。因為當深厚的理論積淀經過創作實踐的淬煉,審美感受力將淪肌浹髓,審美洞察力則擘兩分星。還是用他研究羅爾純先生畫風時所作的判斷為例:從印象主義光色顫動的微妙變化中看到了瞬間的永恒,從納比畫派斑駁的色塊分布和光影的構成中找到形式的生成,從野獸派熾熱的狂放的線條和單純的色彩中悟得圖像的精神意義,從立體派的空間錯位中更堅信解構與重構的價值。當然,楚漢浪漫及盛唐詩韻所展示出的豪放與率真,簡約與激情以及先民們的造型智慧都油然融入。
在他造形的世界里,恍惚著莫迪利亞尼(Amedeo Modigliani)與漢代木俑的神韻、雷諾阿(Auguste Renoir)與鄉野泥娃娃的純厚、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與江南小鎮的幾何抽象……天空、大地、建筑與人構成一個律動的整體。人與環境的關系非生活事理的情節和敘事,而是形的契合與恒久的造型邏輯,這些均組成他視覺藝術的版圖。
在這里,吳為山僅用短短百字就已將畫家的風格出處一一點出,品鑒作品時的幽微心理成為一種融匯了反復涵泳與直覺感悟且不乏詩意的表達。不用過多引述,這部書已充分展示了作者卓越的文字功力,其明顯的文學性論述不僅脫離了令人乏味的濃濃“理論腔” ,即便以文學作品的標準衡量,其價值亦不遑多讓。
《美在中國美術館》的內容談古論今,融貫中西;行文風流絕麗,璧坐璣馳,其中的好文章絕不限于以上例舉。此外,該書的裝幀設計也遵循了“出版者說”中提出的“遵循美育特點,弘揚中華美育精神”的初心,簡約而不失強烈,端莊而不失活潑,處處體現著出版者的匠心。正文前還專門插入一張折頁,是與原作等大的由吳為山手寫的前言。其書法既有帖之靈動,也有碑之風骨,雋永秀逸,文意堂堂,與書中的精美插圖相映生輝。事實上,僅憑一篇書評當然不可能說出本書的全部妙處。而它的妙處也恰恰在于表面文字與圖像背后所“隱”藏的信息。所以,閱讀本書時,“對話”比“接受”更為重要——讀者若敞開心扉,細細品味,與那些才情并茂的文字進行深度交流,便自然能看出“文外之重旨”。也只有這個時候,讀者的審美期待才會得到有效拓展,而這本書才真正呈現出它“使玩之者無窮,味之者不厭矣”的精彩。
(作者系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學博士后、東南大學藝術學博士后,碩士生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