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農(nóng)《古佛圖》歷險(xiǎn)記:曾差點(diǎn)被當(dāng)作柴火燒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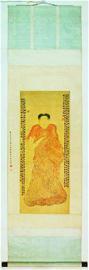
金農(nóng)《古佛圖》
2012年12月,煙臺(tái)市博物館選出“十大鎮(zhèn)館之寶”,其中之一便是“揚(yáng)州八怪”之首金農(nóng)所繪之《古佛圖》。上世紀(jì)60年代初,著名文物鑒賞家張伯駒先生到煙臺(tái),在原煙臺(tái)地區(qū)博物館見到這幅作品,大為震驚,連呼:“了不得!了不得!世界第一!世界第一!”張伯駒感慨地說:“這幅畫我尋找了40多年,以為早已流失海外,沒想到完好地收藏在煙臺(tái),萬幸!萬幸!”之后,不少文物鑒賞家和著名書畫家慕名紛紛到煙臺(tái)欣賞此畫。葉劍英元帥當(dāng)年到煙臺(tái)時(shí),亦曾興奮地觀賞了這幅被國家書畫鑒定組確定為國家一級(jí)文物的傳世佳作。
正如張伯駒先生所說,作為一件稀世珍品,金農(nóng)的《古佛圖》能流傳下來,的確是一件“萬幸”之事,在曲折的流傳過程中,它甚至差點(diǎn)被當(dāng)作“柴火”燒掉!近日,記者在煙臺(tái)市博物館欣賞到了這幅作品,并且從博物館藏品管理部主任李華杰那里,了解到了一段步步驚心的“國寶歷險(xiǎn)記”。
從濰縣“丁家花園”到黃縣“丁百萬”家族
李華杰之所以對《古佛圖》的流傳經(jīng)歷如此了解,是因?yàn)樗母赣H李經(jīng)章就是這個(gè)故事的當(dāng)事人之一。
說起《古佛圖》的流傳,要從濰坊十笏園說起。十笏園是中國北方袖珍式園林建筑,始建于明代,原是明朝嘉靖年間刑部郎中胡邦佐的故宅。清光緒十一年(公元1885年),被濰縣首富丁善寶以重金購得,從此稱作“丁家花園”。金農(nóng)《古佛圖》就藏于十笏園中。
世事變遷,《古佛圖》后來進(jìn)入了黃縣“丁百萬”家族。“丁百萬”家族非常傳奇,鼎盛時(shí),其豪華建筑覆蓋大半個(gè)黃縣城,達(dá)三千余間。丁氏家族系當(dāng)鋪世家,世代重視讀書、做官、經(jīng)商,他們“以學(xué)入仕,以仕保商,以商養(yǎng)學(xué)”。將官、商、儒三者做到有機(jī)結(jié)合,因而長盛不衰。據(jù)記載,丁氏家族的當(dāng)鋪、錢莊遍及全國11個(gè)省市,資產(chǎn)相傳等于清政府一年的財(cái)政收入,成為山東首富,因此綽號(hào)“丁百萬”。由于丁氏家族以開當(dāng)鋪為主,因此也搜進(jìn)了大量珍貴的文物古玩,其中一件便是金農(nóng)的《古佛圖》。
然而,再昌盛的家族也禁不住歷史這輛大車的滾滾車輪。當(dāng)歷史車輪駛到上世紀(jì)40年代,變故降臨,稀世文物的命運(yùn)也出現(xiàn)了變數(shù)。
稀世文物差點(diǎn)被當(dāng)作“柴火”燒掉
上世紀(jì)40年代,膠東地區(qū)進(jìn)行土改,打土豪、分田地,地主家首當(dāng)其沖。黃縣“丁百萬”家族自然也難以幸免。丁家主人跑了,很多沒來得及帶走的財(cái)產(chǎn)就被老百姓分了。
話說丁家有一個(gè)長工,姓林,是黃縣城西松嵐村人。主人跑了、財(cái)產(chǎn)被分了之后,他沒法繼續(xù)干長工了,于是就回了家。回家之后老婆質(zhì)問他:“別人都分了東西,你怎么空手回來了?”老林說,“平日里主人對我挺厚道,不好意思拿他家的東西。”老婆說,“你這個(gè)傻瓜,你不拿,不是照樣被別人拿嗎?”老林一想,老婆說得也對,這是大勢所趨,不拿白不拿,于是就趕了回去。回去一看,屋里的東西,能拿的都被拿走了,找了一圈,只在院子里發(fā)現(xiàn)了兩捆字畫,可能是主人走得著急沒來得及拿,也可能是別人在分財(cái)產(chǎn)的時(shí)候不屑拿,老林就順手把它們拿回了家。
回家之后,老婆又把他熊了一頓:“你拿個(gè)家具還能有點(diǎn)用,就是拿個(gè)瓢子還能盛個(gè)糧食什么的。瞧你拿的這兩捆什么東西,燒火都用不上!”老林一看,字畫都是裝裱過,的確不適合燒火,就順手把它們丟到了自己家的閣樓上。
這一放,就是十幾年。
“柴火”換來1800元“巨款”
時(shí)間到了上世紀(jì)60年代。
1963年,作為煙臺(tái)地區(qū)博物館的負(fù)責(zé)人之一,李華杰的父親李經(jīng)章到黃縣去收字畫,當(dāng)時(shí)去的是原來一戶國民黨軍官的家。博物館的人到鄉(xiāng)下收字畫,村民都很好奇,老林聽說之后也來看熱鬧。他問李經(jīng)章:“這些東西,我家也有兩捆,你們還要嗎?”李經(jīng)章聽了覺得很奇怪:要說國民黨軍官家里有字畫不稀奇,一個(gè)普通農(nóng)民家里怎么會(huì)有這種東西?雖然心里半信半疑的,但他還是跟著去了老林家。
到了家,老林從閣樓上拿下了兩捆布滿灰塵的字畫,李經(jīng)章打開一看,的確有不少好東西,于是就跟老林說先拿回?zé)熍_(tái)鑒定一下。老林很豪爽,說:“國家需要,拿走就行,不用給錢,放著反正也沒用。”李經(jīng)章把東西帶回?zé)熍_(tái)后,對兩捆字畫進(jìn)行了仔細(xì)鑒定,發(fā)現(xiàn)總共70多幅字畫中,有50多幅都是比較有價(jià)值的,其中就有金農(nóng)《古佛圖》這件珍品。
雖是稀世珍品,但國家也不能白拿老百姓的東西,李經(jīng)章于是申請到了1800元財(cái)政經(jīng)費(fèi),親自跑到黃縣送到了老林家。老林拿到1800元錢,非常感動(dòng),“真沒想到,兩捆柴火值這么多錢,公家辦事就是不坑人!”那個(gè)時(shí)候,農(nóng)民辛苦一年也賺不到幾塊錢,在農(nóng)村,30多塊錢就能蓋間房子,1800元可是一筆不折不扣的“巨款”。消息傳開,村民們都很感動(dòng),覺得人民政府辦事“還真靠譜”。
就這樣,差點(diǎn)被當(dāng)做“柴火”燒掉的珍貴《古佛圖》終于到了博物館,此后沒多久,張伯駒先生就在煙臺(tái)看到了這幅畫,于是就出現(xiàn)了本文開頭所寫的那一幕。
“游絲描”、“金錯(cuò)刀”體現(xiàn)極高藝術(shù)價(jià)值
如今,這幅金農(nóng)的《古佛圖》安靜地陳列在煙臺(tái)市博物館,以杰出的藝術(shù)價(jià)值和文物價(jià)值,迎接來來往往的人們細(xì)細(xì)品味。
這幅《古佛圖》為絹本設(shè)色,縱117厘米,橫47.2厘米,圖中釋迦,正面全身,頭頂青螺結(jié),身著紅袈裟,一臂袒露拱手佇立,神態(tài)安詳而肅穆。面部以剛勁的鐵線描勾出,敷設(shè)淡彩,豐腴圓潤,神采飄逸。佛像周身的衣紋采用枯筆折絕畫法,下接卷云蓮座,線條展轉(zhuǎn)流動(dòng),有升騰動(dòng)蕩之感。又于釋迦兩側(cè)作記,右邊文曰:“十五年前為暖鶉居士寫金剛經(jīng)卷,刻之棗木,精裝千本,善施天下名勝禪林……今又畫佛,畫菩薩、畫羅漢,將俟世之信心,敬俸者鋟摹上石,一如寫經(jīng)之流傳云。七十四雙機(jī)郡金農(nóng)記。”左邊題《古佛頌》,長達(dá)百余字。書體楷中兼隸,有“漆書”之稱,其風(fēng)格獨(dú)絕,書畫和諧,使佛像更為突出。
李華杰說,金農(nóng)(公元1686年-1763年)年方五十方始學(xué)畫,由于學(xué)問淵博,瀏覽名跡眾多,又有深厚書法功底,終成一代名家。金農(nóng)留世的畫作很少,這幅《古佛圖》將書法技法融入繪畫之中,是一幅用傳統(tǒng)筆墨“寫”出來的繪畫作品,是金農(nóng)的代表作,畫中運(yùn)用“游絲描”、“金錯(cuò)刀”等技法,顯示出了極高的藝術(shù)價(jià)值,“畫面兩側(cè)金農(nóng)獨(dú)創(chuàng)的漆書題跋,字體前無古人后無來者,與畫相得益彰,實(shí)為稀釋珍品。”
“八怪”之首,獨(dú)創(chuàng)“漆書”
對書畫作品的價(jià)值而言,藝術(shù)水準(zhǔn)是一方面,作者的名氣和歷史地位也很重要。作為“揚(yáng)州八怪”之首,金農(nóng)是核心人物。他在詩、書、畫、印以及琴曲、鑒賞、收藏方面都稱得上是大家。他從小研習(xí)書文,文學(xué)造詣很高,但天性散淡,因此傳世書畫作品很少。
金農(nóng)生活在康、雍、乾三朝,因此他給自己封了個(gè)“三朝老民”的閑號(hào)。他初不以工書為念,然書法造詣卻成為“揚(yáng)州八怪”中最有成就的一位,特別是他的行書和隸書均有著高妙而獨(dú)到的審美價(jià)值。有專家表示,金農(nóng)的書法藝術(shù)以古樸渾厚見長,他首創(chuàng)的漆書,是一種特殊的用筆用墨方法。“金農(nóng)墨”濃厚似漆,寫出的字凸出于紙面,所用的毛筆,像扁平的刷子,蘸上濃墨,行筆只折不轉(zhuǎn),像刷子刷漆一樣。這種方法寫出的字初看起來粗俗簡單,無章法可言,其實(shí)是大處著眼,有著磅礴的氣韻。
金農(nóng)50歲才開始學(xué)習(xí)繪畫,但“涉筆即古,脫盡畫家之習(xí)”,并申言,要把自己“平生高岸之氣”,一一見諸畫中,“以抒不平鳴”。在一幅《墨竹圖》中,他竟然直書:“磨墨五升,畫此狂竹,不釣陽鱭,而釣諸侯也。”
金農(nóng)等人戴上“八怪”的桂冠后,既為社會(huì)所認(rèn)可,又被人們津津樂道,廣為傳揚(yáng)。這除了藝術(shù)風(fēng)格的原因之外,其中也包含著個(gè)性行為、思維方式、處世觀念等多種異于常情的因素。也正是金農(nóng)深厚的學(xué)養(yǎng)和清高的品性,使得他在后世名氣越來越大,在“西泠印社2009年秋季藝術(shù)品拍賣會(huì)”上,金農(nóng)的《花果冊》以3976萬元的價(jià)格創(chuàng)下西泠拍賣最高成交紀(jì)錄。
(編輯:曉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