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雜志上的中國——寫在《人民中國》創(chuàng)刊60年之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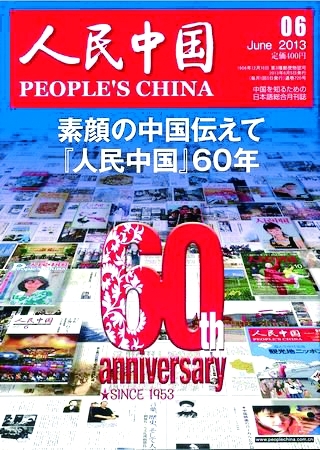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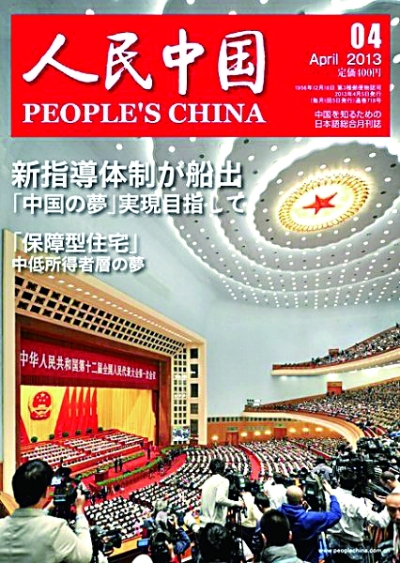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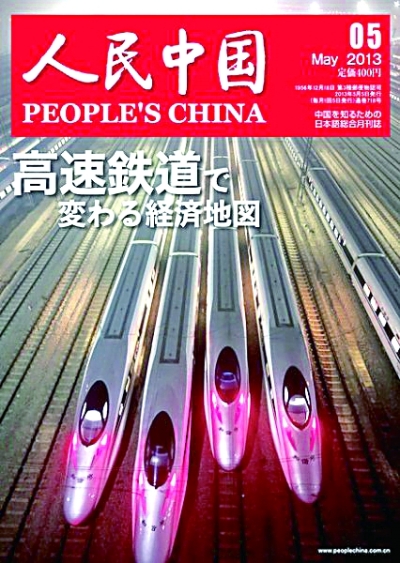
對(duì)于國內(nèi)的讀者,知道《人民中國》的人也許不多,但在日本,許多人對(duì)它耳熟能詳。
上世紀(jì)50年代初,西方國家企圖將新生的中國窒息在封鎖之中。1950年1月,《人民中國》英文版創(chuàng)刊。從此,新中國向世界打開了第一扇窗,新中國的聲音從這里傳向世界。
在周恩來、廖承志等中央領(lǐng)導(dǎo)的關(guān)懷、支持下,1953年6月,《人民中國》日文版創(chuàng)刊。創(chuàng)刊號(hào)的封面上,是剛剛過去的那個(gè)“五一”國際勞動(dòng)節(jié),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接受少先隊(duì)員獻(xiàn)花的照片。
最初的日子讓文化部原副部長(zhǎng)、《人民中國》日文版創(chuàng)建者之一的劉德有先生至今無法忘懷。“當(dāng)時(shí),手里拿著還散發(fā)著油墨味的創(chuàng)刊號(hào),人人都激動(dòng)不已。特別是那些幫助我們工作的日本朋友,想到這本雜志不久就會(huì)到達(dá)他們的祖國,更是激動(dòng)萬分。”
今天,在日本仍活躍著不少《人民中國》的讀書會(huì)。《人民中國》的讀者既有普通民眾,也有官員政要。原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現(xiàn)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都是《人民中國》的自費(fèi)訂戶。《人民中國》總編輯王眾一還把雜志送到了福田康夫、鳩山由紀(jì)夫、野田佳彥三位當(dāng)時(shí)在任的日本首相手上。
在很長(zhǎng)的一段歷史時(shí)期內(nèi),《人民中國》是關(guān)心中國的日本友人了解中國的唯一窗口和橋梁。《人民中國》雜志社社長(zhǎng)陳文戈說:“下一步,我們將把《人民中國》打造成聚集權(quán)威觀點(diǎn)、解讀社會(huì)現(xiàn)象、展現(xiàn)魅力文化、促進(jìn)中日人民交流的全新媒體和公關(guān)服務(wù)平臺(tái)。”
雜志上呈現(xiàn)的中國原汁原味
“我的家鄉(xiāng)在江蘇省長(zhǎng)江以南的小鎮(zhèn)戚墅堰,它緊緊地依傍著大運(yùn)河。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時(shí)代,就是在那兒度過的……對(duì)孩子來說,運(yùn)河更是他們不可缺少的伙伴……一到夏天,大家?guī)缀跽於寂菰诤永铮蛘咴妥幼矫圆兀窈⒆犹稍谀赣H的懷抱里,盡情地?fù)潋v,撒嬌;或者帶個(gè)小木盆,邊玩邊摸螃蟹,逮小蝦。夜里夢(mèng)中也激蕩著運(yùn)河的波浪和水聲……”
這是《人民中國》記者沈興大、劉世昭騎自行車采訪京杭大運(yùn)河后,筆端呈現(xiàn)的中國。
“……走了三個(gè)半小時(shí),我們于中午十二點(diǎn)半到了培石鎮(zhèn)。路上只遇到過四位從湖北省巴東縣買了一群山羊趕回巫山縣去的農(nóng)民,我問他們?yōu)槭裁床怀舜哌@100來公里的棧道,他們講趕著這群羊乘船船票就太貴了。原來他們選擇棧道是出于經(jīng)濟(jì)上的原因……”
上世紀(jì)90年代初,攝影記者劉世昭徒步走三峽,讓人們?cè)诩?xì)部感受著真實(shí)的中國。
就是在這樣的無數(shù)細(xì)節(jié)中,《人民中國》向它的讀者生動(dòng)地勾勒出中國的發(fā)展變化,抒發(fā)著生活在其間的中國人的喜怒哀樂。
60年,720期,《人民中國》將一個(gè)深入細(xì)部、生動(dòng)鮮活的中國,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他們的報(bào)道,被同行們稱為“人民中國體”。
用腳走出來的報(bào)道
說到“人民中國體”,有些往事不能不提。
“我的文章是用腳走出來的”。這句話,雖然出自《人民中國》日本專家村山孚先生之口,卻是《人民中國》記者們共同的遵循。
村山孚的采訪實(shí)踐,是對(duì)此話的最好注腳。那次他去北大荒852農(nóng)場(chǎng)采訪,去田頭,進(jìn)廠房,到職工家里拜訪,和工人們座談,采訪從早晨6:20持續(xù)到晚上10點(diǎn)。他說:“只有親眼所見,寫出的文章才有說服力。”
車慕奇做了一輩子記者。即使是做了總編輯和退休后,也沒有放下手中的筆,直到生命的終點(diǎn)。“作為記者不能嬌氣,不管什么地方,只要人能到的地方,我就能去;人能睡的地方,我就能睡;人能吃的,我就能吃。”他身體力行的追求,被奉為《人民中國》記者的圭臬。
走進(jìn)基層,走進(jìn)生活,需要勇氣,需要堅(jiān)忍,有時(shí),還會(huì)有生命危險(xiǎn)。
為拍到瀘沽湖的美景,攝影記者沈延太天沒亮就只身爬上湖邊的山頂,天黑了才拖著疲憊的身體返回駐地;為采訪鄂溫克獵民的狩獵點(diǎn),高級(jí)記者丘桓興雪夜中,在大興安嶺狼群出沒的原始森林里徒步跋涉8個(gè)小時(shí)。
康大川把年輕編輯關(guān)在自己家中,管吃管住,為的是把鮮活的采訪素材寫成讀者愛看的報(bào)道文章;車慕奇踏遍大西北寫出《絲綢之路》;丘桓興遍訪各族群眾寫下《中國民俗探索》;孫戰(zhàn)科的《重返北大荒》,更是融進(jìn)了20多年流放生涯的思考與感悟……“記者的腳印能延伸多遠(yuǎn),讀者的視線就能延伸多遠(yuǎn),思緒也會(huì)隨著作者的腳步和仰天俯地的筆觸和鏡頭而行步。”這是《人民中國》采訪者、寫作者的共識(shí)。
心在走近,距離就不會(huì)遙遠(yuǎn)
中日友好21世紀(jì)委員會(huì)中方首席委員唐家璇在寫給《人民中國》的信中說:《人民中國》向廣大日本朋友開啟了一扇絢麗多彩、真實(shí)親和的“中國之窗”。
《人民中國》是座橋,建橋者不僅是編輯、記者,做通聯(lián)工作的亦有獨(dú)特貢獻(xiàn)。1964年,于淑榮來到《人民中國》,在通聯(lián)崗位上一直干到退休。30多年中,經(jīng)她回過信的讀者,累計(jì)達(dá)上萬人次。讀者在信中寫道:“我將把它(《人民中國》的回信)珍藏起來,把人民中國社充滿誠意的心,告訴給日本的人們。每當(dāng)我想起給了我許多關(guān)照的先生們,就好像心中點(diǎn)亮了一盞明燈,時(shí)時(shí)溫暖著我的心。”
《人民中國》工作著幾代日本專家。“人民中國體”的日語敘述,由于他們的努力,更加精彩。劉德有回憶說:“我們的譯稿經(jīng)日本專家稍微一改,就明顯提升了一個(gè)檔次。”
曾榮獲中國政府友誼獎(jiǎng)、如今已經(jīng)71歲的橫堀克己繼續(xù)擔(dān)任著《人民中國》的編輯顧問,參與著《人民中國》的制作。他說:“《人民中國》的許多報(bào)道是日本媒體沒有刊登過的。這些信息絕非推測(cè)或無法確認(rèn),而是權(quán)威負(fù)責(zé)、可信度高的信息。當(dāng)下的日本,有關(guān)中國的不實(shí)消息泛濫,因此,《人民中國》不失其存在的意義。”
在日本專家群體中,池田亮一、戎家實(shí)、金田直次郎是為《人民中國》工作著的時(shí)候離開這個(gè)世界的。他們的名字將永存于《人民中國》的史冊(cè)。
“希望《人民中國》立足中日關(guān)系大局,進(jìn)一步發(fā)揮‘以心交流’的傳統(tǒng)與特色,凝聚中日關(guān)系的正能量,為促進(jìn)中日人民友好交流和兩國關(guān)系健康、穩(wěn)定發(fā)展作出新的貢獻(xiàn)。”在《人民中國》甲子華誕之時(shí),中國外文出版發(fā)行事業(yè)局局長(zhǎng)周明偉這樣寄語。
在世界激蕩的風(fēng)雷中,甲子之年的《人民中國》再次出發(fā),去續(xù)寫“一本雜志上的中國”新篇章。(本報(bào)記者 莊 建)
(編輯:偉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