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人文遺址,“人文”保護
長城、秦始皇陵、絲綢之路……一處處或線性或區域性的大遺址,往往具備中華文明象征符號、知名旅游景點等特質,其所具有的經濟、文化與社會價值,讓我們不能用傳統意義上的遺址保護方式來對待。經過多年努力,如今大遺址保護架構已經從開辦博物館轉變為遺址公園建設,如何建立起既符合“遺址”要求又適應“公園”需求的有效機制和工作思路,則成為文物工作者需要思考的新課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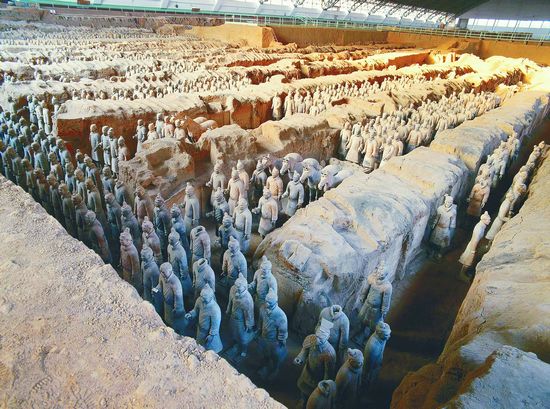
鴻山遺址公園讓窮村富起來
2010年,鴻山遺址公園被評定為全國首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在鴻山遺址的規劃、保護和開發過程中,該遺址公園積極探索將文化保護、生態修復、農業轉型、旅游發展等方面有機結合的模式,因地制宜地解決了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農業產業化、農民增收等突出問題,實現了遺址保護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互動推進。
在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方面,規劃實施了農民安置小區建設、路網工程、污水管網鋪設、環境綠化美化工程等。目前,已有921戶、3176人住進了專門配套建設的環境優美、設施齊全的農民安置小區,其余村民則保持原居住狀態,但周邊環境、生活配套設施也得到了大幅提升。在農民增收方面,對農業和旅游兩大產業進行統一規劃實施,逐步形成了以特色高效產業和旅游配套產業雙輪驅動的富民產業體系,為遺址區百姓提供多種致富道路,帶來了“真金白銀”。
在旅游開發與策劃方面,始終貫徹“保護為主、合理利用”的宗旨,在堅決保護珍貴歷史文化遺產的基礎上,增強文物保護項目的旅游功能,突出旅游項目的文化生態導向,統籌發展文化旅游產業。已開放的旅游項目有鴻山遺址博物館、濕地生態展示區和農業生態展示區等,在此基礎上,還以鴻山遺址公園為核心,整合周邊的泰伯墓、泰伯廟、昭嗣堂、錢穆故居等一批重量級文化遺產,開辟了大遺址考古之旅、生態濕地之旅、農業生態觀光之旅等旅游專題。目前,鴻山遺址公園年游客量達到20萬人次,帶動了餐飲、住宿、休閑、購物等一系列旅游配套產業,區域內年營銷收入達到1.3億元,文化旅游產業初具規模,鴻山也已從偏僻的鄉村成功轉型為文化生態旅游勝地。

曲江遺址公園雨景
甑皮巖遺址公園讓歷史“活”起來
甑皮巖遺址是華南地區重要的新石器時代洞穴遺址,甑皮巖遺址公園則是第一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立項名單中占地面積最小的遺址公園。在過去的近兩年時間里,該遺址公園不與其它大遺址比規模、比投入、比速度,而是圍繞甑皮巖遺址的特點,結合遺址面積小、出土文物觀賞性不強但學術價值較高等實際情況,按照“以小見大”的總體思路,在考古研究、遺址保護、考古科普、發展旅游及招商融資等方面積極探索,尋求甑皮巖遺址從考古文化遺址向考古遺址公園轉變,并融入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科學途徑。
甑皮巖遺址公園的開放目標是從生態環境、文化內涵上讓甑皮巖文化立體地“活”起來,成為普通大眾可以形象感知、通俗品讀的文化產品。為此,在不違背《甑皮巖遺址保護規劃》的基礎上,把甑皮巖遺址的保護展示與旅游項目策劃有機結合,依據考古研究成果規劃在遺址公園內恢復甑皮巖遠古生態環境,模擬展現先民的部落生活情景,營造中外游客與“甑皮巖人”時空錯位相遇、零距離接觸的文化體驗,同時建設生態型遺址博物館、洞穴考古學術交流中心、模擬考古體驗中心、游客服務中心、甑皮巖文化廣場、時空隧道、遠古文化街等基礎景觀設施。
2009年還策劃建設了甑皮巖模擬考古樂園,2010年建設了模擬考古發掘區、原始作坊、原始狩獵場、原始篝火場等設施,成為青少年模擬考古科普基地。先后舉辦了30多期模擬考古體驗活動,參與中小學生人數達到12000多人次,推出的模擬考古發掘、萬年古陶仿制、原始石器仿制、投射動物模型、鉆木取火體驗、原始火鍋品味等集看、聽、玩、嘗為一體,互動性、參與性較強的考古科普活動,滿足了青少年求知、求奇、求樂的多元需求。
記者觀察
大遺址保護的開放思維
本報記者 云菲
近期,一則關于某遺址公園的負面新聞占據了各媒體顯要位置,據當地市民反映,該園內出現了城墻裂縫、地面塌陷、景觀破壞、雜草叢生等現象,讓他們甚感惋惜。這暴露出大遺址保護工作存在亟待解決的問題,但換個角度看,則說明大遺址保護正逐漸成為民眾關注的焦點、熱議的話題乃至自覺的行動。
大遺址,是指規模特大、文物價值突出的大型文化遺址;建立遺址博物館或遺址公園,是保護、展示、研究、利用大遺址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國家文物局有關資料表明,我國正在向以“六片、四線、一圈”為核心、150處大遺址為支撐、覆蓋全國的大遺址保護新格局邁進;很多地方政府也以前所未有的熱情投入到大遺址保護和遺址公園建設中來。從“遺址”到“大遺址”再到“遺址公園”,不僅是稱謂的簡單變化,更是理念的深刻變革,但這也標志著大遺址保護工作在雙重目標審視下必須步入一個新階段。
在各地大遺址保護實踐過程中,有一點不可回避,那就是大遺址上原住民的生產生活與文物保護展示之間面臨的矛盾。有數據顯示,漢長安城城垣遺址內現有54個行政村,涉及5萬多人;三星堆遺址保護范圍內共有11個行政村,其中6平方公里的重點保護范圍共涉及5個行政村1500余戶、4500余人,人口密度達到每平方公里754人。水源利用對文化地層的滲透侵蝕、房舍搭建帶來的布局凌亂和垃圾廢物的傾倒堆置等人為活動,勢必會不同程度地對文物遺跡的安全和遺址環境的協調造成影響。由此可見,大遺址保護并非單一的文物個體保護,還涉及人口、土地、環境等諸多問題,是一項牽動經濟、社會、生態發展的系統工程,這也意味著,大遺址保護不僅是專業人員的行為,更應是全民的行為,不僅是行業的行為,更應是社會的行為。于是,當大遺址保護工作進入新階段后,作為人文領域的大遺址,選擇“人文”思路開展保護、利用漸成趨勢。
在金沙遺址,在開城遺址,當地政府都不約而同地加強了遺址保護范圍內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環境衛生治理、道路交通規劃等工作,開城遺址環境整治工程更是使牽涉其中的3個自然村有了向外連接的砂石路,解決了村民出行難的問題。在安陽,當地政府將宮殿宗廟區所在地小屯村、后母戊鼎發現地武官村以及大司空村,改造成歷史文化民俗村,組織村民開展殷商文化、民俗展示等旅游服務,增加了農民收入。應當看到,在大遺址保護過程中,美化了遺址地生態環境,提高了原住民生活質量,更促進了區域產業布局和功能轉型,民眾因此切實感受到了實實在在的好處。反過來,這也更好地激發出民眾對于文物保護的熱情,支撐他們持久地參與到大遺址保護的行動中來。
“保護”不是“看護”,將文物遺跡科學、合理、有效地展示給公眾是遺址保護的最終目的,更是促成大遺址保護事業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手段。以唐長安城延平門遺址公園、曲江遺址公園為代表的大遺址市民公園模式所實施的開放式保護,受到了很多群眾的歡迎。2010年入選首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的殷墟遺址,積極利用研究和考古成果,拓展衍生出多種類型的文化工程和文化產品,籌建中國文字博物館、中國考古博物館、殷墟車馬坑博物館,制作3D動漫電影每天循環播放,以生動、直觀的形式展示殷商時期的歷史風貌和傳說故事,彌補了殷墟遺址觀賞性弱的不足。靈武市通過優化游覽線路和觀光項目,使過去無人問津的水洞溝遺址,從只局限于科學考察的高端人群,發展成為吸引大量普通游客的寧夏又一處重要文化旅游場所。這些無疑都是很好的例子。
從專門的文物保護工程到推動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文化工程,讓文化遺產保護成果真正惠及于民的“人文”思路、開放思維,更好地釋放了大遺址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值得肯定,更值得推廣。
(編輯:孫育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