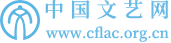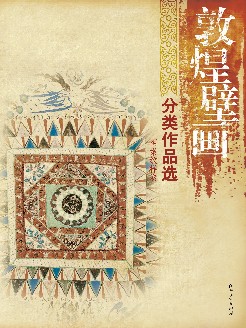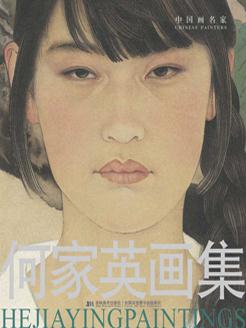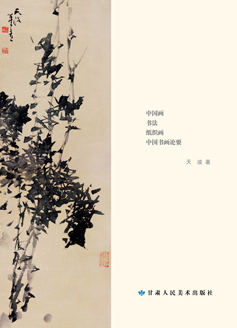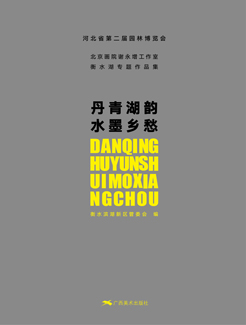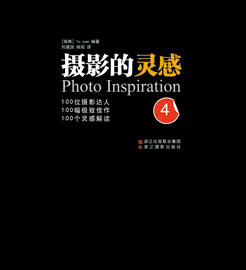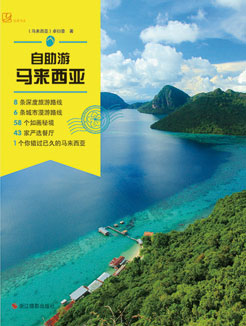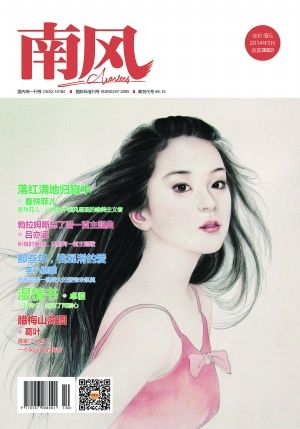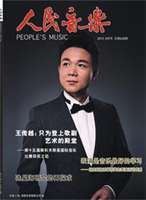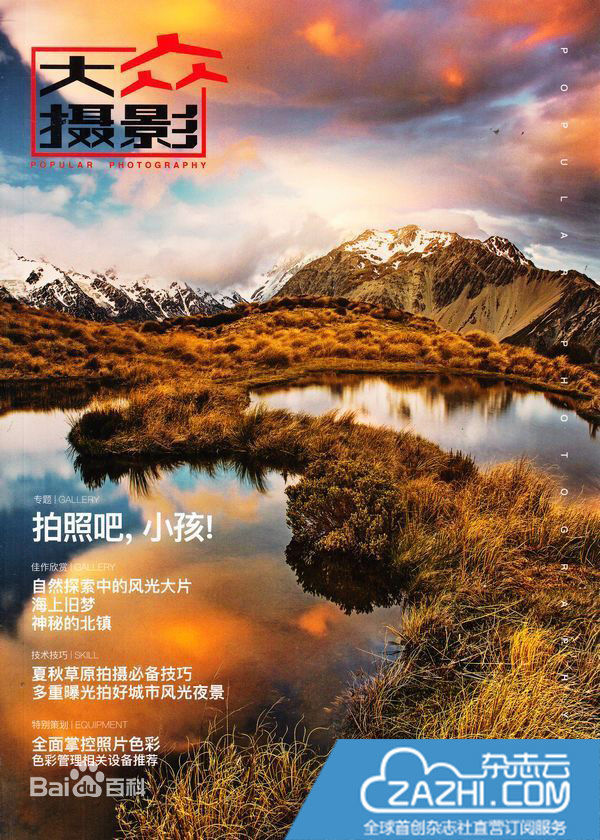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并不是萬(wàn)能的,如果不從真正的文化建設(shè)出發(fā),不從中國(guó)自己的本土道路出發(fā),它會(huì)割傷我們民族文化復(fù)興的希望。

杭間 清華大學(xué)美術(shù)學(xué)院副院長(zhǎng) 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
“中國(guó)制造”在近20年中經(jīng)歷了復(fù)雜的變化。它從一個(gè)讓人自豪的名詞變成尷尬和反思中國(guó)產(chǎn)品的形容詞,它是中國(guó)經(jīng)濟(jì)從鄉(xiāng)鎮(zhèn)經(jīng)濟(jì)模式開始快速進(jìn)入全球化經(jīng)濟(jì)系統(tǒng)的產(chǎn)物,但由于“中國(guó)設(shè)計(jì)”的缺席,“中國(guó)制造”墜入了低水平、為人做嫁衣的境況之中。
歐美各國(guó)的環(huán)保政策使我國(guó)制造業(yè)輝煌下的外患與內(nèi)憂更加凸顯。從國(guó)際上看,遵循環(huán)保法規(guī)已不是一次性的個(gè)別事件,以短期糾正方式或以被動(dòng)反應(yīng)方式在產(chǎn)品中遵守環(huán)保法規(guī),已使我國(guó)制造業(yè)疲于應(yīng)付而逐漸失去優(yōu)勢(shì)。從國(guó)內(nèi)環(huán)境看,“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發(fā)展模式難以為繼,能源、資源、環(huán)境已直接影響到我國(guó)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的調(diào)整和增長(zhǎng)方式的轉(zhuǎn)變。比較發(fā)達(dá)國(guó)家而言,中國(guó)的經(jīng)濟(jì)模式仍然不是理想的,因?yàn)楸阋说摹爸袊?guó)制造”背后有許多問題,單從設(shè)計(jì)的高附加值來(lái)看,我們的便宜加工就是一個(gè)低層次的行為。設(shè)計(jì)界呼吁政府重視設(shè)計(jì)已經(jīng)有些年頭了,但是從一些有關(guān)設(shè)計(jì)協(xié)會(huì)的生存狀況來(lái)看,依然是不被重視的。上世紀(jì)80年代初期的一段時(shí)間,政府有關(guān)部門開始對(duì)包裝的高附加值加以重視,有了中國(guó)包裝藝術(shù)設(shè)計(jì)協(xié)會(huì)等組織的成立,以及各種各樣包裝雜志的創(chuàng)辦。但是30年過去了,許多政府官員和企業(yè)家對(duì)設(shè)計(jì)的理解還仍然停留在包裝設(shè)計(jì)的階段,產(chǎn)業(yè)界片面追求利潤(rùn)甚至矯枉過正,出現(xiàn)了繁瑣包裝,設(shè)計(jì)在社會(huì)消費(fèi)層面產(chǎn)生了倒退。
上世紀(jì)90年代以來(lái),產(chǎn)業(yè)界開始意識(shí)到通過綠色設(shè)計(jì)、綠色制造獲取“綠色利潤(rùn)”,使我國(guó)制造業(yè)進(jìn)入綠色發(fā)展通道,實(shí)現(xiàn)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重要性。綠色設(shè)計(jì)是面向產(chǎn)品全生命周期的設(shè)計(jì)。產(chǎn)品生命周期是指從原材料生產(chǎn)、產(chǎn)品生產(chǎn)制造、裝配、包裝、運(yùn)輸、銷售、使用直至回收重用及處理處置所涉及的各個(gè)階段的總合。絕大多數(shù)民營(yíng)企業(yè)家甚至包括中國(guó)很多大中型企業(yè)的企業(yè)家都認(rèn)為,要把“中國(guó)制造”改造成“中國(guó)創(chuàng)造”,必須要靠設(shè)計(jì),而且要?jiǎng)?chuàng)新品牌管理經(jīng)營(yíng)。進(jìn)入21世紀(jì),中國(guó)必須樹立自己的品牌,這個(gè)過程,就是中國(guó)由世界消費(fèi)大國(guó)向世界經(jīng)濟(jì)強(qiáng)國(guó)邁進(jìn)的過程。
在這樣的前提下,通過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來(lái)整合設(shè)計(jì)與產(chǎn)業(yè)之間的關(guān)系成為政府與企業(yè)間的一種共識(shí)。一時(shí)間,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在中國(guó)已經(jīng)遍地開花,媒體鼓吹不遺余力,政府提倡大張旗鼓,企業(yè)、街道、風(fēng)景名勝區(qū)一起動(dòng)作,讓人恍惚覺得中國(guó)的文化和產(chǎn)業(yè)已經(jīng)有美好的未來(lái)。
但在熱鬧的表象下,很少有人去追究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的本來(lái)含義是什么,人人都在說的這個(gè)詞更像是一種任意可以曲解的“真言”,各自向著有利于自己意愿的方面闡釋,從而達(dá)到某種目的。其實(shí),在眾說紛紜的表述中,各國(guó)都有結(jié)合自己產(chǎn)業(yè)特點(diǎn)和利益的表述,但聯(lián)合國(guó)教科文組織給出的定義似乎較為客觀:“文化產(chǎn)業(yè)指的是結(jié)合創(chuàng)造、生產(chǎn)與商品化等方式,去運(yùn)用本質(zhì)是無(wú)形的文化內(nèi)容。這些內(nèi)容基本上受到著作權(quán)的保障,其形式可以是貨品或是服務(wù)。”定義的本質(zhì)是商業(yè)和文化互動(dòng)下的“貨品或服務(wù)”,這是一個(gè)很有策略的表述,它把這個(gè)新興產(chǎn)業(yè)最具爭(zhēng)議的究竟是“文化”重要還是“產(chǎn)業(yè)”為主,通過最終的目標(biāo)的描述“貨品或服務(wù)”給延伸了,從而避免了像歐美或日本有關(guān)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的姓“商”姓“文”的長(zhǎng)久爭(zhēng)議。
現(xiàn)在看來(lái),一個(gè)成功的文化產(chǎn)業(yè)項(xiàng)目推出后,最終都回歸到資本。如果說最好的設(shè)計(jì)是最受消費(fèi)者歡迎的設(shè)計(jì),那它同時(shí)也是給資本投入者帶來(lái)巨大利潤(rùn)的設(shè)計(jì)。那些熱烈歡迎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給文化帶來(lái)新生的人可能沒有想過,讓資本進(jìn)入文化領(lǐng)域,永遠(yuǎn)只是資本擁有者的策略而已。同時(shí),在日益覺醒的社會(huì)大眾的理性面前,它更是一種妥協(xié)之舉。上世紀(jì)60年代中期歐美國(guó)家出現(xiàn)的“社會(huì)指標(biāo)運(yùn)動(dòng)(the social indicators movement)”,是由于知識(shí)分子不滿當(dāng)時(shí)政府的指標(biāo)系統(tǒng)(如GDP)將社會(huì)發(fā)展簡(jiǎn)單看成經(jīng)濟(jì)產(chǎn)值的表現(xiàn),而促使政府積極強(qiáng)調(diào)和發(fā)展“社會(huì)指標(biāo)”,以彌補(bǔ)經(jīng)濟(jì)指標(biāo)所無(wú)法測(cè)量出來(lái)的問題,包括環(huán)境污染、生活品質(zhì)、社會(huì)公平等。從上世紀(jì)90年代開始,學(xué)者們更認(rèn)識(shí)到,一般指標(biāo)系統(tǒng)無(wú)法充分呈現(xiàn)文化發(fā)展的現(xiàn)況與問題,因而修正社會(huì)指標(biāo)系統(tǒng)倡導(dǎo)建立適合于文化發(fā)展的指標(biāo)系統(tǒng)。于是,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便成為各方都能接受的選擇。
但文化產(chǎn)業(yè)的本質(zhì)并沒有因此而改變。由于“資本”的介入,不可避免地帶來(lái)了片面追求“剩余價(jià)值”的商品經(jīng)濟(jì)的本能特性。例如所謂“好設(shè)計(jì)”是極大地調(diào)動(dòng)人類消費(fèi)欲望的設(shè)計(jì),而不必考慮社會(huì)資源的合理分配、節(jié)約和環(huán)境保護(hù),手機(jī)讓人眼花繚亂的更新?lián)Q代就是一個(gè)最典型的陰謀,很難說清楚是設(shè)計(jì)師成為資本家的同謀,還是消費(fèi)者心甘情愿被宰割,還是大眾時(shí)尚的最可恥的異化。新馬克思主義德國(guó)法蘭克福學(xué)派以“文化工業(yè)”來(lái)批判文化商品化對(duì)文化的殘害,就是由此產(chǎn)生的有代表性的觀點(diǎn)。
“文化搭臺(tái)、經(jīng)濟(jì)唱戲”在幾年前是有相當(dāng)代表性的用語(yǔ),這幾年雖然沒有人再提,但對(duì)于相當(dāng)級(jí)別的政府官員而言,這種觀念依然存在,甚至根深蒂固,這就使得中國(guó)的文化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情形變得更為復(fù)雜,往往在一出轟轟烈烈的文化工程“開演”以后,不久就變了樣。而最具核心價(jià)值的“創(chuàng)造”的含義往往被視而不見。對(duì)傳統(tǒng)文化而言,它在現(xiàn)代社會(huì)的重生需要?jiǎng)?chuàng)造性發(fā)展,而不是“舊瓶裝新酒”。要做到這一點(diǎn),對(duì)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的保護(hù)意義重大,美國(guó)人當(dāng)年最早立法保護(hù)專利并定為重要的國(guó)策,是教訓(xùn)沉痛后的結(jié)果。不如此,一個(gè)民族就不能有效地保護(hù)“創(chuàng)新”進(jìn)而得到發(fā)展,從某種意義上說,“創(chuàng)新”和“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是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發(fā)展最重要的兩翼。但是,中國(guó)的文化產(chǎn)業(yè)對(duì)此的表現(xiàn)是軟弱無(wú)力和曖昧的。其結(jié)果,在贏得微薄得可憐的利潤(rùn)的同時(shí),既誤導(dǎo)了文化的消費(fèi)者也使中國(guó)的現(xiàn)代文化有長(zhǎng)久地淪為侏儒的危險(xiǎn)。
不可否認(rèn),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在改變“中國(guó)制造”的產(chǎn)業(yè)模式的時(shí)候,確實(shí)給中國(guó)這個(gè)世界上最大的發(fā)展中國(guó)家?guī)?lái)了前所未有的機(jī)遇,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的改變、就業(yè)率的提高、文化品質(zhì)的全球化等等,但應(yīng)該看到,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并不是萬(wàn)能的,而是一把雙刃劍,如果不從真正的文化建設(shè)出發(fā),不從中國(guó)自己的本土道路出發(fā),它會(huì)割傷我們民族文化復(fù)興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