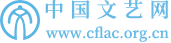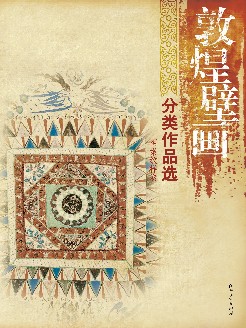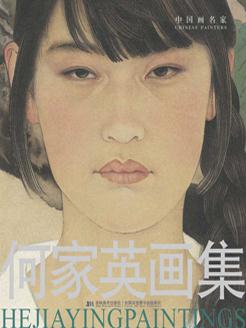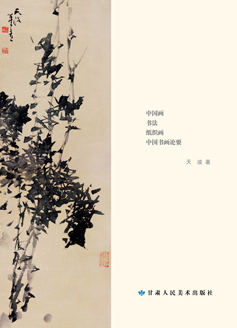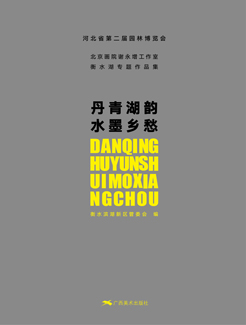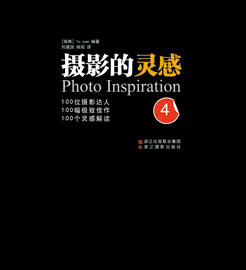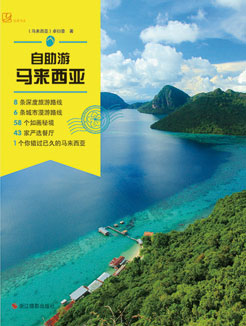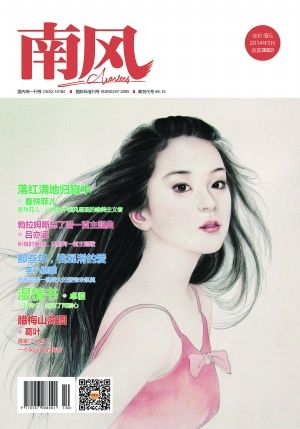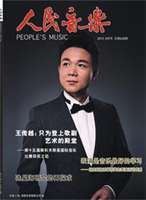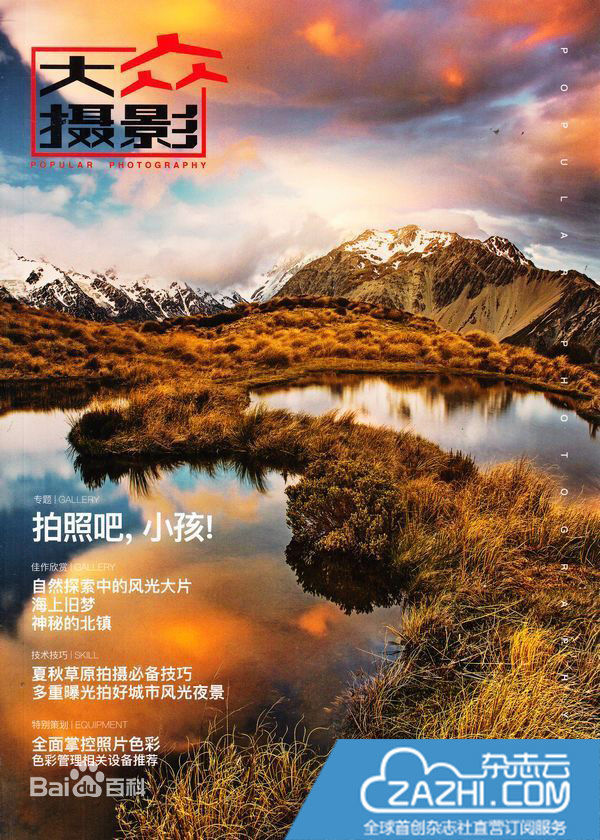“延安文藝”作為一種文藝現(xiàn)象,一般特指從1935年10月中國(guó)工農(nóng)紅軍經(jīng)過(guò)二萬(wàn)五千里長(zhǎng)征到達(dá)陜北,至1948年春中共中央離開(kāi)陜北這15年中,以延安為中心、包括陜甘寧邊區(qū)和其他革命根據(jù)地在內(nèi)的革命文學(xué)藝術(shù)。
今年5月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huì)上的講話》發(fā)表70周年紀(jì)念。隨著眾多親歷者的先后離世,搶救收集第一手原始資料,整理還原“延安文藝”本有的格局和情景,系統(tǒng)記述中國(guó)革命文藝洪流的形成和發(fā)展,以典籍的形態(tài)將這一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下來(lái),讓“延安文藝”的活化石留存后世,已經(jīng)刻不容緩,需要分秒必爭(zhēng)。
一
“延安文藝”最值得重視的價(jià)值,在于它凝聚了“人民文藝”的基本精神:文藝來(lái)自人民生活,文藝要為人民服務(wù),文藝家要和人民結(jié)合。——這是一條通過(guò)人民結(jié)合達(dá)到為人民服務(wù)的文藝發(fā)展道路,這條道路是由“延安文藝”在實(shí)踐中踏勘出來(lái)、而由《講話》在理論上總結(jié)出來(lái)的。這個(gè)永恒的命題,是“延安文藝”生命之所系,也是一切文藝生命之所系。不論時(shí)代如何發(fā)展、文藝如何變化,“人民文藝”這一基本精神是長(zhǎng)青的。
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huì)上的講話》,是“延安文藝”運(yùn)動(dòng)指導(dǎo)性和總結(jié)性的文件。毛澤東從“延安文藝”運(yùn)動(dòng)鮮活的實(shí)踐出發(fā),從文學(xué)藝術(shù)的美學(xué)價(jià)值和社會(huì)使命入手,對(duì)歷史實(shí)踐主體與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主體的關(guān)系作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xué)解答。人民是歷史實(shí)踐的主體,人民的選擇是歷史的最終選擇,也是藝術(shù)的最終選擇。文藝的美學(xué)價(jià)值最終體現(xiàn)為文藝在何種程度上反映了這一歷史實(shí)踐主體在歷史進(jìn)程中的業(yè)績(jī)和主動(dòng)性,以及他們?cè)跉v史實(shí)踐活動(dòng)中表現(xiàn)出來(lái)的精神形象——性格、心理、感情、情緒等等。這既是作品社會(huì)價(jià)值的主要體現(xiàn),也是作品藝術(shù)魅力的主要體現(xiàn)。
文藝如何將新的生活美轉(zhuǎn)化為新的藝術(shù)美?“延安文藝”和《講話》在理論和實(shí)踐的結(jié)合上總結(jié)出一條唯物主義反映論的路子,這便是要求文藝工作者長(zhǎng)期地、無(wú)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nóng)兵群眾中去,然后進(jìn)入創(chuàng)作過(guò)程。丁玲、歐陽(yáng)山、柳青、李季等正是遵循這條路子,塑造了一大批已經(jīng)成為歷史主人的新的工農(nóng)兵形象的作品,開(kāi)創(chuàng)了新的生活美轉(zhuǎn)化為新的藝術(shù)美之先河。
《講話》進(jìn)而提出,作家藝術(shù)家要為人民大眾服務(wù),就有一個(gè)改變自己的立足點(diǎn)和思想感情的問(wèn)題。毛澤東提出了要改變文藝工作者對(duì)人民大眾不熟不懂的狀況,要深入生活和群眾結(jié)合,學(xué)習(xí)他們,描寫(xiě)他們,同時(shí)教育他們和提高他們。文藝來(lái)自人民生活,文藝要為人民服務(wù),文藝家要和人民結(jié)合,——《講話》緊緊抓住“人民”這一核心價(jià)值,由此出發(fā),展開(kāi)論述了文藝與革命、文藝與生活、普及與提高、作家世界觀的改造、文藝批評(píng)標(biāo)準(zhǔn)等一系列問(wèn)題,成為指導(dǎo)人民文藝發(fā)展的思想體系,引領(lǐng)了整個(g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時(shí)期的人民文藝實(shí)踐。這使“延安文藝”當(dāng)之無(wú)愧被譽(yù)為中國(guó)當(dāng)代人民文藝的淵藪和圭臬。
歷史上一切進(jìn)步的、優(yōu)秀的文藝作品,總是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與人民的生活和人民的情緒保持著某種深刻的聯(lián)系。“延安文藝”運(yùn)動(dòng)和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完美結(jié)合,使馬克思主義的人民文藝觀得到了創(chuàng)造性發(fā)展。《講話》的理性精神通過(guò)大眾化的“延安文藝”運(yùn)動(dòng),轉(zhuǎn)化為整個(gè)社會(huì)的藝術(shù)行為,在千百萬(wàn)老百姓的實(shí)踐和心靈中開(kāi)花結(jié)果,乃至造就了一個(gè)中國(guó)文藝的燦爛時(shí)代。
二
五十四年前(1958年)我第一次讀《講話》,記得當(dāng)時(shí)最真切的感受便是它的開(kāi)拓創(chuàng)新精神,便是它的察人之未察、言人之未言的勇氣與氣度,以及包蘊(yùn)于其中的創(chuàng)造激情、思考穿透力和表述的鮮明與機(jī)智。以后每讀一次,使我怦然心動(dòng)的都是這種創(chuàng)新激情與開(kāi)拓精神。正是這種感受,激發(fā)了一個(gè)普通讀者與那位偉大作者之間的共鳴和交流,點(diǎn)燃了潛藏于心的創(chuàng)造激情,拓寬了自己的眼界和胸襟,也誘使我進(jìn)一步去探尋《講話》的開(kāi)拓性思維結(jié)構(gòu)和思維方法。
每一項(xiàng)社會(huì)實(shí)踐,每一種物質(zhì)的、精神的產(chǎn)品,給予歷史的都有好幾個(gè)層次的留存。首先是這一產(chǎn)品在具體實(shí)踐中包含的物質(zhì)和理論的既在性成果。其次是含納在某項(xiàng)社會(huì)實(shí)踐或物質(zhì)、精神成果中的結(jié)構(gòu)性內(nèi)容。再次是實(shí)踐主體或創(chuàng)造主體固化在某項(xiàng)社會(huì)實(shí)踐活動(dòng)或物質(zhì)、精神產(chǎn)品中的特有的情緒心理內(nèi)容。
我也是從這幾個(gè)層次來(lái)理解“延安文藝”和《講話》的。“延安文藝”和《講話》留給歷史的,既包含著毛澤東從“延安文藝”實(shí)踐中提煉出來(lái)的一系列具有中國(guó)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觀點(diǎn)和文藝方針政策,以及“延安文藝”成功的實(shí)踐;也包含著毛澤東在提出、闡述他的觀點(diǎn)時(shí)表現(xiàn)出來(lái)的開(kāi)放性思維結(jié)構(gòu)和創(chuàng)造性思維方法,以及流貫于“延安文藝”運(yùn)動(dòng)中的那種自由開(kāi)放的、極富創(chuàng)造性的情緒狀態(tài)。這幾個(gè)層次,都是《講話》留下的精神財(cái)富,在過(guò)去70年乃至今后,都會(huì)對(duì)我國(guó)的文化藝術(shù)深遠(yuǎn)地發(fā)揮作用。
在三個(gè)層次上,“延安文藝”和《講話》的內(nèi)在氣質(zhì)都是開(kāi)放、開(kāi)拓、創(chuàng)新的。
從既在性內(nèi)容的層次看,“延安文藝”和《講話》的歷史首創(chuàng)精神和思想啟蒙作用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gè)方面:一是對(duì)文學(xué)藝術(shù)的美學(xué)價(jià)值和社會(huì)使命的關(guān)系,對(duì)歷史實(shí)踐主體與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主體的關(guān)系,作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xué)解答并用藝術(shù)實(shí)踐作了驗(yàn)證。如前所述,這種解答既是反映論的、又是辯證法的。古往今來(lái),能夠?qū)⑦@個(gè)眾說(shuō)紛紜的問(wèn)題解答得如此深刻而又淺顯,如此具有真理意義、又有中國(guó)特色,恐非“延安文藝”和《講話》莫屬。二是從生活與藝術(shù)的關(guān)系入手,在理論與實(shí)踐的結(jié)合上有力地促進(jìn)了新的現(xiàn)實(shí)美轉(zhuǎn)化為新的藝術(shù)美這一精神創(chuàng)造過(guò)程。
歷史唯物主義者主張,生活是藝術(shù)的源泉,美客觀地存在于人類的社會(huì)生活之中。“延安文藝”和《講話》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并印證了這一觀點(diǎn)。問(wèn)題不止于此,當(dāng)歷史發(fā)展到了人民大眾已經(jīng)由被壓迫被剝削者翻身作了主人,而且在革命根據(jù)地建立了自己的政權(quán),開(kāi)始有了自主的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生活時(shí),社會(huì)生活新的根本性的變化,必然產(chǎn)生新的美。如何將這種新的生活美(包括新的人物、新的精神面貌、新的社會(huì)實(shí)踐和生活圖畫(huà))轉(zhuǎn)化為新的藝術(shù)美,是延安文藝工作者所面臨的新課題,也是他們能以建立新的人民文藝,為中國(guó)乃至世界文藝寶庫(kù)做出新貢獻(xiàn)的歷史機(jī)遇。
三
從結(jié)構(gòu)性內(nèi)容的層次看,“延安文藝”和《講話》在文化結(jié)構(gòu)、思維結(jié)構(gòu)和思想方法上,多方面表現(xiàn)出創(chuàng)新和開(kāi)放特色。這不僅與《講話》作者毛澤東的文化構(gòu)成和思維結(jié)構(gòu)有關(guān),也是延安文藝運(yùn)動(dòng)、延安文化人、乃至我們黨整個(gè)領(lǐng)導(dǎo)層文化構(gòu)成和思維結(jié)構(gòu)的一種聚光。
毛澤東青年時(shí)代的中西文化交匯,在后來(lái)的革命生涯中升華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guó)文化傳統(tǒng)和革命現(xiàn)實(shí)斗爭(zhēng)的結(jié)合。為準(zhǔn)備《講話》,毛澤東在延安文藝界作了大量的調(diào)查研究,研究中外哲學(xué)和美學(xué),重讀《魯迅全集》,讀俄國(guó)民主主義批評(píng)家“別、車、杜”的論著。知識(shí)結(jié)構(gòu)的多維會(huì)給思維結(jié)構(gòu)的開(kāi)放以重大影響。
從延安當(dāng)時(shí)的文化環(huán)境來(lái)看,也是比較開(kāi)放和重視融匯的。且不說(shuō)“中國(guó)新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是以西洋文學(xué)的輸入而開(kāi)始的”(周揚(yáng))這樣一個(gè)五四以來(lái)就形成的大文化背景,就拿陜甘寧邊區(qū)來(lái)說(shuō),文藝工作者相當(dāng)一部分是從淪陷區(qū)、國(guó)統(tǒng)區(qū)聚匯而來(lái),其中不少人在歐美和日本、東南亞學(xué)習(xí)或生活過(guò),直接受過(guò)西方和東方文化的影響,他們構(gòu)成邊區(qū)傳播和應(yīng)用世界文化的重要因子。反法西斯戰(zhàn)爭(zhēng)的世界性決定了中國(guó)抗戰(zhàn)文藝的世界性,延安是中國(guó)抗戰(zhàn)文藝的中心,中國(guó)抗戰(zhàn)文藝是世界反法西斯文藝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使“延安文藝”在精神上、題材上、藝術(shù)追求上與當(dāng)時(shí)的世界文化有著血緣的聯(lián)系。
這種開(kāi)放的文化氛圍和文化結(jié)構(gòu),是《講話》唯物辯證法理論建構(gòu)和思維方法的重要成因之一。毛澤東從中國(guó)社會(huì)和文藝的實(shí)際出發(fā),緊緊抓住文藝與人民的關(guān)系這個(gè)主要矛盾,以此為立足點(diǎn)來(lái)解決其他問(wèn)題,在論述各種問(wèn)題時(shí)又總是在兩種或多種要素的結(jié)合中來(lái)建構(gòu)理論框架。
《講話》不只是一般地談多種因素的結(jié)合,還具體分析各種因素交互作用的矛盾運(yùn)動(dòng)過(guò)程,也指出各種因素在結(jié)合過(guò)程中可能產(chǎn)生的不平衡狀態(tài)。比如,強(qiáng)調(diào)現(xiàn)階段中國(guó)文化不是封建的或殖民地的文化,也不是社會(huì)主義文化,而是“無(wú)產(chǎn)階級(jí)領(lǐng)導(dǎo)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新民主主義文化。它首先是為工農(nóng)兵的,同時(shí)也把城市小資產(chǎn)階級(jí)勞動(dòng)群眾和知識(shí)分子包括在服務(wù)對(duì)象中。他既批判了“寧要大眾不要藝術(shù)”,強(qiáng)調(diào)政治忽略藝術(shù)的觀點(diǎn),又批評(píng)了強(qiáng)調(diào)藝術(shù)否定政治,主張“藝術(shù)至上”或“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的觀點(diǎn)。這就抵制了“左”的和右的傾向。
《講話》認(rèn)為為人民服務(wù)的方向和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規(guī)律是一致的,因而重視文學(xué)藝術(shù)的美學(xué)意義,強(qiáng)調(diào)文藝的典型化原則,主張對(duì)中國(guó)和外國(guó)豐富的遺產(chǎn)和優(yōu)良傳統(tǒng),要繼承、借鑒、為我所用。《講話》明確指出,革命文藝家要學(xué)習(xí)馬克思主義,但“學(xué)習(xí)馬克思主義是要我們用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觀點(diǎn)去觀察世界、觀察社會(huì)、觀察文學(xué)藝術(shù),而不是要我們?cè)谖乃囎髌分袑?xiě)哲學(xué)講義。馬克思主義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學(xué)中的原子論、電子論”。這里,既反對(duì)蘇聯(lián)拉普派那樣簡(jiǎn)單地用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代替文藝創(chuàng)作方法,又批評(píng)了否定世界觀對(duì)創(chuàng)作的指導(dǎo)作用的傾向。《講話》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革命文藝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頭腦中反映的產(chǎn)物,既重視作品的客觀性(“人民生活”),又重視作家的主體性(“作家頭腦”)。也正是由此出發(fā),毛澤東強(qiáng)調(diào)了作家深入生活(客體)和改造世界觀(主體)的同等重要性,等等,都無(wú)不充滿了辯證法。
四
從情緒性內(nèi)容這個(gè)層次看,在“延安文藝”和《講話》中,鮮明地流貫著一種思想啟蒙者、精神解放者和文化開(kāi)拓者那種自由、自主、自信的精神狀態(tài)和情緒狀態(tài)。這種情緒狀態(tài)是一切歷史進(jìn)步期和社會(huì)上升期的主流精神狀態(tài),也是一切創(chuàng)造者、拼搏者的主流精神狀態(tài)。它會(huì)超越具體的行業(yè)、具體的時(shí)代、具體的歷史實(shí)踐,對(duì)人類生命和每個(gè)人的生命起引燃、激揚(yáng)作用。
毛澤東是五四運(yùn)動(dòng)這一中國(guó)現(xiàn)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運(yùn)動(dòng)的參與者,是在那一代思想啟蒙者和開(kāi)拓者的精神氛圍中成長(zhǎng)起來(lái)的,而且在以后的革命實(shí)踐中發(fā)育和成熟了自己精神創(chuàng)造者的心態(tài)。延安時(shí)期是中國(guó)現(xiàn)代史上的第二次思想解放運(yùn)動(dòng)。毛澤東是這次思想解放運(yùn)動(dòng)的發(fā)動(dòng)者和引領(lǐng)者。《講話》與先后發(fā)表的《反對(duì)黨八股》《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以及活躍的邊區(qū)文藝運(yùn)動(dòng),所表現(xiàn)出來(lái)的磅礴氣度和創(chuàng)造激情,使我們能以將潛藏在其中的情緒性內(nèi)容和第二次思想解放運(yùn)動(dòng)的博大精神氣度交融為一體,讓你那么真切地感受到了一個(gè)新歷史時(shí)代的脈搏——
那是敢于面對(duì)新的現(xiàn)實(shí),鮮明地提出新問(wèn)題,創(chuàng)造性地解決新問(wèn)題,開(kāi)拓新的思考路子、理論路子和實(shí)踐路子的創(chuàng)新意識(shí);
那是善于抓住機(jī)遇,從社會(huì)的整體環(huán)境和宏觀格局中,借助歷史推力,果斷解決某一方面問(wèn)題的歷史智慧;
那是在廣泛深入的調(diào)查研究、平等真摯的討論討教中,在傳統(tǒng)、現(xiàn)實(shí)、未來(lái)的交集中,集思廣益、博采眾長(zhǎng),凝聚新思路的開(kāi)放融匯精神;
那是重視理論與實(shí)踐相結(jié)合,并能迅即將啟蒙的思考轉(zhuǎn)化為廣大民眾的共識(shí),轉(zhuǎn)化為社會(huì)實(shí)踐行為,轉(zhuǎn)化為新的文化藝術(shù)模式,而進(jìn)入歷史的文化實(shí)踐力、執(zhí)行力;
那是論者和實(shí)踐者在從事精神創(chuàng)造時(shí),能夠充分發(fā)揮自己的創(chuàng)造素質(zhì)和潛力,而進(jìn)入一種自如、自信、自主的最佳精神狀態(tài);
中國(guó)作風(fēng)、中國(guó)氣派、中國(guó)智慧,創(chuàng)新的內(nèi)容、創(chuàng)新的思維、創(chuàng)新的激情——這就是我們從“延安文藝”和《講話》中強(qiáng)烈感受到的。
五
堅(jiān)持、發(fā)揚(yáng)“延安文藝”傳統(tǒng)和《講話》的精神,開(kāi)創(chuàng)社會(huì)主義文藝的新局面,就要堅(jiān)持它的基本精神,既包括堅(jiān)持它富于歷史首創(chuàng)精神的既在性內(nèi)容,也包括堅(jiān)持它多維開(kāi)放的結(jié)構(gòu)性內(nèi)容,更包括它自由創(chuàng)造、積極開(kāi)拓的情緒性內(nèi)容。
歷史發(fā)展到今天,我們的文藝面臨著全方位發(fā)展、創(chuàng)新的歷史新課題。“延安文藝”和《講話》關(guān)于“人民文藝”觀的三大要點(diǎn)(文藝來(lái)自人民生活,文藝要為人民服務(wù),文藝家要和人民結(jié)合)所涉及到的六個(gè)主題詞:“文藝”、“文藝家”、“人民”、“人民生活”、“服務(wù)”、“結(jié)合”,幾經(jīng)歷史性變遷,內(nèi)含有了極大的豐富和發(fā)展。“人民”的內(nèi)容變了,“人民生活”(包括精神生活)的內(nèi)容和形式變了,“文藝”的面貌也變了,“文藝家”的思想藝術(shù)素養(yǎng)變了,文藝為人民服務(wù)的路子寬了,文藝家與人民結(jié)合的目的任務(wù)方法手段也豐富多樣了。在這每一個(gè)變化中,都有著創(chuàng)新、拓展的廣闊天地。
而且,現(xiàn)代人知識(shí)構(gòu)成的變化和現(xiàn)代科學(xué)特別是思維科學(xué)的發(fā)展,既印證了、也極大地豐富了馬列主義的認(rèn)識(shí)論和辯證法,使我們思考文藝各類問(wèn)題有了更好的條件。改革開(kāi)放以來(lái),第三次思想解放運(yùn)動(dòng)蓬勃興起,奉實(shí)踐為檢驗(yàn)真理的標(biāo)準(zhǔn),在鄧小平理論和科學(xué)發(fā)展觀指導(dǎo)下,現(xiàn)代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引發(fā)了社會(huì)生活的深刻變化,引發(fā)了政治、文化和價(jià)值觀念的深刻變化,中華民族更是進(jìn)入了一個(gè)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物質(zhì)生產(chǎn)力和精神生產(chǎn)力大解放的新時(shí)期,這更為我們繼承發(fā)揚(yáng)“延安文藝”和《講話》的基本精神提供了最好的歷史機(jī)遇和社會(huì)環(huán)境。我們要不辜負(fù)時(shí)代的要求,承擔(dān)起這一歷史責(zé)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