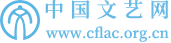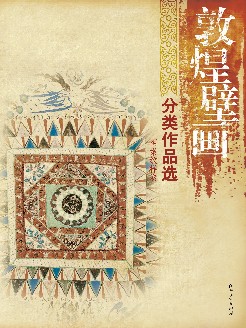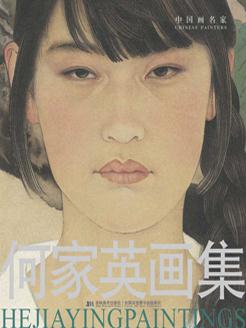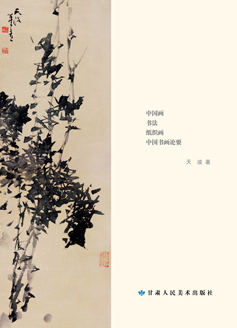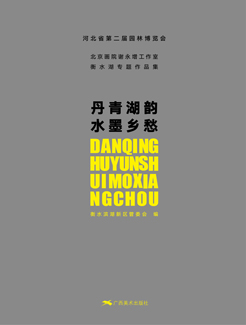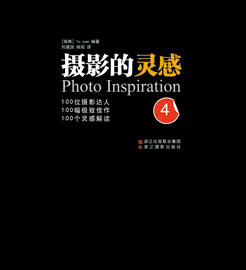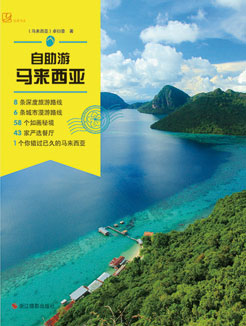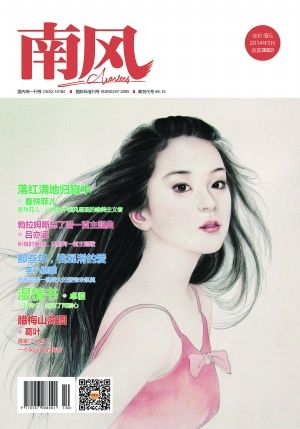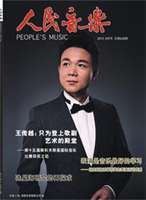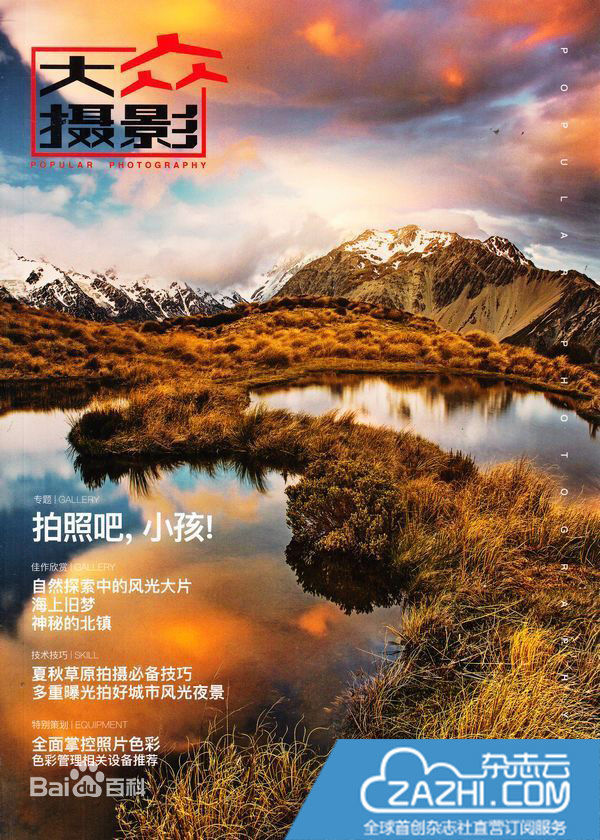追尋“中國(guó)精神”的歌劇探索
|
——中國(guó)歌劇舞劇院推出歌劇《蘇武》的背后
近日,由中國(guó)歌劇舞劇院創(chuàng)排的大型民族原創(chuàng)歌劇《蘇武》在北京保利劇院首演。作為國(guó)字號(hào)藝術(shù)院團(tuán)重點(diǎn)推出的新作,該劇的藝術(shù)特點(diǎn)和創(chuàng)作過程備受關(guān)注。
精心塑造鮮活的蘇武
時(shí)光閃回,宏大的場(chǎng)面、斑駁的古城墻、起伏跌宕的情節(jié),在光與影的交織中,一部輝煌的史詩(shī)在舞臺(tái)上緩緩書寫。
“要讓每個(gè)人心中的蘇武化作中國(guó)歌劇舞臺(tái)上的鮮活形象實(shí)屬不易。”歌劇《蘇武》導(dǎo)演陳子度深有感慨地說,“歌劇《蘇武》力圖打破傳統(tǒng)表述方式,以歷史劇的莊重與傳奇劇的曲折相統(tǒng)一、思想的風(fēng)骨與異域的風(fēng)情相統(tǒng)一、歌劇的規(guī)格和規(guī)范與舞臺(tái)元素多樣化表現(xiàn)手段相統(tǒng)一為創(chuàng)作宗旨。”
談及創(chuàng)作歌劇《蘇武》的初衷,中國(guó)歌劇舞劇院院長(zhǎng)林文增坦言:“作為國(guó)家級(jí)的藝術(shù)院團(tuán)要有責(zé)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創(chuàng)作新劇目時(shí)應(yīng)該選擇弘揚(yáng)高尚情懷的素材和主題。蘇武是真實(shí)的歷史人物,他身上所表現(xiàn)出來(lái)的高尚氣節(jié)、家國(guó)情懷值得現(xiàn)代人學(xué)習(xí)。同時(shí),創(chuàng)排《蘇武》還兼具了強(qiáng)化歌劇本體、打造人才團(tuán)隊(duì)的目的。”
厚重而不笨重,古樸而不陳舊。為了突出戲劇性和人物角色的思想內(nèi)涵,這部歌劇以交響樂為主體,吸納并融匯了歌劇、音樂劇、清唱?jiǎng) ⑶榫皠〉冗m合音樂表現(xiàn)和情景表演的元素,營(yíng)造出了一種特殊的歷史厚重感。無(wú)論是大氣悲壯的《我的名字叫蘇武》,還是深具家國(guó)情懷的《我是一架風(fēng)箏》等詠嘆調(diào),都力圖從不同側(cè)面刻畫出蘇武歷盡艱辛、留居匈奴19年持節(jié)不屈最終回歸故土的心路歷程。在藝術(shù)表現(xiàn)上,整場(chǎng)演出通過多種舞臺(tái)調(diào)度、燈光變化,展現(xiàn)出蘇武內(nèi)心深處對(duì)美好的向往和對(duì)平靜生活的渴望。
青年演員成中堅(jiān)力量
為了確保歌劇《蘇武》演出成功,劇院主創(chuàng)人員傾注了全部的心血。精通歌劇音樂的專業(yè)干部李小祥寸步不離“戰(zhàn)場(chǎng)”;負(fù)責(zé)“里應(yīng)外合”的副導(dǎo)演朱亞林有空就到排練廳督戰(zhàn);蘇武的扮演者毋攀為了這次苦戰(zhàn),曾經(jīng)悄悄地駐扎在練琴房里,吃透了《蘇武》全部樂譜,將歌劇中的鼓點(diǎn)與音樂的節(jié)點(diǎn)起承轉(zhuǎn)合、縱橫交錯(cuò)了然心中。
當(dāng)距離首演還有4個(gè)小時(shí),演員們身上還穿著厚厚的演出服,一遍遍地反復(fù)走臺(tái),沒有一個(gè)人離開……
在中國(guó)歌劇面臨人才困境的時(shí)候,中國(guó)歌劇舞劇院能擁有眾多的青年力量,很是難得。這得益于劇院十幾年來(lái)開展的人才培養(yǎng)計(jì)劃。每次創(chuàng)排新劇目,劇院都公開選拔角色,從舞臺(tái)歷練、形象氣質(zhì)、性格特點(diǎn)以及倫理思想等方面實(shí)施青年演員定向培養(yǎng),從而為劇院培養(yǎng)了一大批中堅(jiān)力量。
探索民族化之路
“這些年中國(guó)歌劇創(chuàng)作雖然風(fēng)格、題材多樣,但并未出現(xiàn)一部劃時(shí)代意義的經(jīng)典作品。”一位歌劇愛好者說。據(jù)統(tǒng)計(jì),我國(guó)現(xiàn)有原創(chuàng)歌劇100多部,數(shù)量不可謂少,不過真正叫得響、有影響力的作品卻是屈指可數(shù)。“如今貼近大眾、貼近生活,能引起人們心理和情感共鳴的劇目越來(lái)越少了。”有觀眾反映。
“我們現(xiàn)在很多歌劇的創(chuàng)演者往往不顧欣賞對(duì)象、根植的土壤和大眾的喜好,一味地往‘高精尖’上拔,往‘洋大全’上靠,這就使歌劇有意或無(wú)意地處于居高臨下的位置。”朱亞林認(rèn)為,歌劇作為來(lái)自西方的藝術(shù)形式,給中國(guó)的創(chuàng)作者最直接的課題就是:應(yīng)該借鑒什么、舍棄什么?如果取舍不當(dāng),就會(huì)造成形式和內(nèi)容嚴(yán)重脫節(jié),就會(huì)因非洋非中、不倫不類而脫離大眾。
陳子度也直言,首演后褒貶之聲都有,從謝幕的第二天起他和朱亞林就開始了修改整排工作。“我們深知,一出戲不可能推出來(lái)就是精品。”陳子度說,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一個(gè)關(guān)鍵前提是給誰(shuí)看,這部作品反復(fù)籌劃,劇本先后六易其稿,力圖打破傳統(tǒng)表述方式,以“歸零”的心態(tài)找到獨(dú)特的藝術(shù)氣質(zhì)和思想含量,實(shí)現(xiàn)突破創(chuàng)新。
從今年5月起,中國(guó)歌劇舞劇院持續(xù)發(fā)力、新作連連。歌劇《蘇武》已被列入由文化部主辦的2013年國(guó)家藝術(shù)院團(tuán)優(yōu)秀劇目展演,民族歌劇《鴻雁》、舞劇《孔子》等已進(jìn)入全面創(chuàng)作階段,將陸續(xù)呈現(xiàn)給觀眾。中國(guó)歌劇舞劇院將盡全力將這幾部作品打造成具有中國(guó)精神、中國(guó)特色、中國(guó)氣派的優(yōu)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