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文學中有一種很天真的東西
阿瑟·克拉克的墓碑上刻著一句話:“他從未長大,但從未停止成長。”這正是科幻文學的核心。
科幻文學中有一種很天真的東西
近年來,隨著劉慈欣的《三體》三部曲熱銷40萬套,國內掀起了一股科幻熱潮。在此環境下,今年舉行的第四屆全球華語科幻星云獎的入圍名單中,科幻小說的數量和質量都比前幾屆大有進步,科幻作家人數也有所增加,更出現了像排球名將趙蕊蕊這樣的跨界新人。
不僅如此,從去年開始,各大出版機構先后公布了自己的科幻出版計劃;《科幻世界》專門成立了科幻圖書事業部,甚至開始籌劃中國科幻產業園;近 年來嶄露鋒芒的青年作家中,陳奕潞、陳楸帆、寶樹和飛氘四人都簽在了郭敬明旗下,郭敬明欲將他們打造成國內原創科幻的中堅力量,并形成作家-編劇-影視作 品的科幻產業鏈。
然而,科幻文學一派繁榮的景象背后,還有很多冷靜的思考。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系主任江曉原教授表示,大部分人都未認識到科幻文學的思想價值, 科幻文學價值被低估。7月24日,“中國科幻第一人”、第四屆科幻星云獎評委劉慈欣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談到了科幻文學存在的諸多不足之處,他說:“中 國的科幻文學市場還沒有啟動。”對于科幻文學的未來,劉慈欣認為,在這個危機與希望并存的快速變化的社會,有利于科幻文學的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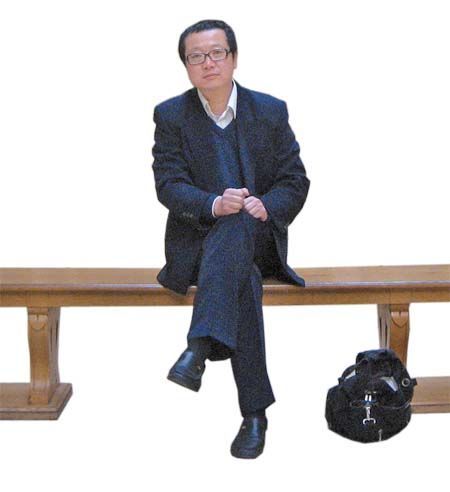
劉慈欣,1963年6月生,中國當代新生代科幻的主要代表作家,中國科普作協會員,山西省作家協會會員。代表作有《超新星紀元》《球狀閃電》“地球往事”系列(《三體》《三體II:黑暗森林》及剛剛出版的《三體:死神永生》)等。
科幻文學迎來“春天”
記者:作為第四屆全球華語科幻星云獎的評委,您對本屆入圍作品有何評價?
劉慈欣:本屆科幻星云獎的入圍作品風格多樣,涉及的題材也很廣泛,有描寫環境問題的,有描寫外來物種入侵的,還有生物學題材等等,但最多的是描寫太空旅行的作品。而且,此次參賽的作品數量更多,質量更高,作者更年輕化。
記者:本屆全球華語科幻星云獎特別設立了少兒科幻獎項,初衷是什么?
劉慈欣:這個獎項設立得好。在上世紀50年代的中國科幻文學熱潮中,出現的全是少兒科幻作品,在人們心目中形成了“科幻文學等同于少兒文學” 的烙印。所以,在上世紀80年代的科幻文學熱潮中,科幻作家、評論家們急于扭轉人們對科幻的印象。但這也產生了一個副作用,就是科幻文學似乎患上了少兒文 學恐懼癥,這直接造成現在國內少兒科幻文學作品的缺乏。
目前國內創作少兒科幻作品比較有成就的只有楊鵬一人,不夸張地說,他一個人撐起了少兒科幻文學的整個天空。其實,少兒科幻是科幻文學中十分重 要的一個領域,因為孩子們需要很多包括科幻文學作品在內的高質量的讀物,而且科幻文學也很適合孩子們在成長的過程中閱讀。科幻文學中有一種很天真的東西, 阿瑟·克拉克的墓碑上刻著一句話:“他從未長大,但從未停止成長。”這正是科幻文學的核心。
所以,設立少兒科幻獎很有意義,我相信,這會對少兒科幻文學的發展起一個很好的推動作用。
記者:這些變化應該和近兩年掀起的科幻文學發展熱潮有關,這股“科幻熱”產生的原因是什么?
劉慈欣:在中國,科幻文學的市場開始出現熱潮有一個深層次的因素。就像上世紀80年代那次科幻熱潮一樣,它的直接背景和推動力就是當時郭沫若 說的“科學的春天”,長期的科學低潮之后,人們開始關注科學技術。中國發展到現在,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都呈現加速的趨勢,它深刻地改變著我們民族的文化視 野和文化氛圍。有一部分中國人開始思考更終極的問題,思考全人類都關心的問題。中國現代化進程帶給了人們新的精神狀態,這就是科幻熱的原因。
記者:近年來,科幻文學受到出版界的重視,郭敬明也簽下了陳楸帆、寶樹等幾位科幻作家,并打算形成作家-編劇-影視作品的科幻產業鏈,這是否為科幻文學提供了一個發展的機遇?
劉慈欣:近兩三年來,科幻文學的市場熱度確實在增加,社會各界都在關注科幻。眾所周知,郭敬明在出版行業的市場運作能力很強,與傳統的科幻出 版機構相比,郭敬明的出版團隊有更多的想法和創造力,而且郭敬明旗下的作家已經擁有廣泛的讀者群,比以前的科幻讀者群大得多,科幻作品能利用這個優勢迅速 擴大影響。
科幻是對人生命的擴展
記者:雖然科幻文學目前處于一個很好的發展時期,但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系主任江曉原教授卻表示,大部分人都未認識到科幻文學的思想價值,科幻文學的價值被低估了。
劉慈欣:科幻文學作為一種類型文學,首先要有文學的基本功能—提供一個好故事,讓讀者產生一種閱讀的愉悅感。
科幻文學的思想價值是更深層次的東西。科幻文學為人們提供了一種思維方式,不像科學那樣嚴謹、受限制,也不像文學那樣天馬行空,它是介于文學和科學之間的一種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可以進行很多思想實驗,把各種各樣的未來排列出來,讓我們對未來有一個更開闊的視野。
科幻也是對一個人生命的擴展。它涉及到的時間、空間都是非常廣闊的,它把我們傳統的主流文學看不到、不愿意看的那些宇宙中的其他部分呈現了出 來。同時,它把人性放到這些部分中去,讓人性在這里面表現出它的美丑、它的本質,這是主流文學從來沒有表現過的,這就是我們需要讀科幻的一個重要原因。
記者:科幻文學和科學的關系密不可分。有人認為,科幻文學是“帶著鐐銬跳舞”—科學能為科幻文學提供想象的基礎,但也會制約科幻文學的創作?
劉慈欣:我的觀點正好相反。科學不是桎梏想象力的鐐銬,反而為想象力插上了翅膀。科學為想象提供了豐富的源泉,比傳統的奇幻、魔幻等幻想小說能提供的多得多,科學所涉及的時間、空間上的廣度,以及科學對自然界的那些最新發現,已經遠遠超出了我們的想象力。
科幻在危機與希望中發展
記者:與西方的科幻文學相比,中國目前的科幻作品,有哪些不足?
劉慈欣:這次評獎,涌現出很多優秀的作品,比如青年科幻作家陳楸帆的《荒潮》,實屬近年來科幻小說的巔峰之作;韓松的《高鐵》,在文學方面很現代,很有穿透力;還有郝靜芳的《回到卡戎》等。但是,這些作品的市場影響力有待提高。
目前中國科幻文學還存在很多不足之處,市場規模和讀者群體都很小,科幻作家人數也不多,長期從事科幻文學創作的只有一二十人,這和主流文學作 家協會會員動輒幾千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此外,科幻影視是空白,很少有具有影響力的科幻電影電視出現。另外,少兒科幻也是一個欠缺的領域。可以說,中國科 幻文學的作者、作品的數量和質量,以及受眾群體的廣泛程度,都和國外科幻文學有著相當大的差距。而最根本、最大的差距是市場規模。美國每年出版1000多 種科幻小說,中國即使在去年科幻文學比較繁榮的情況下,出版的作品也不到100部。
記者:中國科幻文學要培育和發展市場,最迫切需要突破的瓶頸是什么?
劉慈欣:科幻文學在美國有上百年發展歷史,雖然中國的科幻文學起步并不晚,從明末清初就開始了,但是發展斷斷續續,所以美國整個社會對科幻文 學的接受程度比中國要成熟許多,讀者群更加廣泛而穩定,科幻作為一種文化也更成熟,普及率更高。在中國,科幻文學要有市場,必須讓一批科幻作品成為暢銷 書,建立廣泛的讀者群,才能吸引更多的作者投入科幻創作,寫出更多受讀者歡迎的作品,如此反復,良性循環。
另外就是,大部分的出版機構對科幻的運作很不理想,沒有什么突出的成績。特別是一些出版社的營銷方式根本不適合于科幻的。科幻文 學的性質、讀者群都有著自己鮮明的特點,其市場運作也有自己的特點,出版社不能把其他暢銷書的營銷模式套用上來,而是要根據它的特點,制定出適合科幻文學 的營銷方式。
記者:但從目前的創作看,前景依然是可期待的。
劉慈欣:對,目前,中國的大環境正在向有利于科幻文學的方向發展,有點像上世紀初美國科幻黃金時代的社會形勢—舊的東西已經被打破,新的東西 還沒有被建立起來,一切都充滿著又都充滿著危機。這是一個危機和希望并存的快速變化的社會,而科幻文學正是一種描寫變化的文學。現在我們需要的是真正優秀 的作品和到位的出版,但這需要一個過程。
(編輯:曉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