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華:偉大的作家會選擇往艱難的地方走

余華近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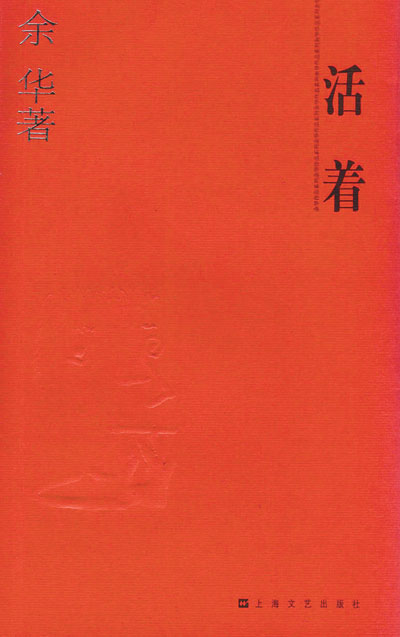
小說《活著》封面
“我是一個觀眾,一個對這個故事非常熟悉的觀眾,但是孟京輝還是給我帶來了陌生感。”在觀眾陣陣掌聲和歡呼聲的簇擁下,站在演出結束卻余溫未消的舞臺上,著名作家余華顯得興奮、激動,甚至有些五味雜陳:“我在下面看著,百感交集,不斷地抹眼淚,現在眼睛還沒干。謝謝所有人!”
被譽為中國內地先鋒派小說代表人物的余華,1992年9月3日,將一部抒寫了真實而艱苦生活的小說《活著》封筆;2012年9月4日,長達3小時零5分鐘的話劇《活著》,首次被搬進國家大劇院的戲劇場。20年一路走來,臺上各位主創、臺下眾多觀眾與余華一道感嘆:經歷了諸多不易,但我們都在共同努力地美好地活著!本報記者在首演后,專訪了作家余華。
“沒有必要忠實原著”
記者:當年看到電影《活著》時,您提出質疑:“怎么不像我的小說了?”那么這一次您如何看待話劇《活著》,之前和孟京輝導演有過什么溝通呢?
余華:從頭到尾我都沒有管,我不想干涉。其實在這個世界上,沒有誰對誰錯,只是人們難免因為對一個東西太過熟悉就把陌生的定義為錯的。幾年前,我和孟京輝在一個意大利朋友家碰面,他當時說要做《許三觀賣血記》,我說可以先做《活著》,之后就全部交給他了。他的想法很多,不斷地變化。
記者:對于之前讀過《活著》原作的讀者,這一次也會不由自主地將兩者進行比較,對此您怎么看?
余華:這是我第一次看由我自己的作品改編的話劇,當年話劇《兄弟》在上海演出的時候,我在北京,沒有過去看,后來他們來北京演,我又在國外,所以沒看成。我要謝謝孟京輝這個團隊,為我們呈現了這么好的舞臺表演,采用了敘述特征,象征主義、表現主義手法什么都有,但絕對不是抽象的,讓我們往情感和人物命運方面聯想,而不是往思想哲學方面聯想。而且演員的演出讓我非常感動,個個情緒都是那么飽滿,尤其是我要說,黃渤謝謝你!20年前我在寫這部小說的時候,一直認為福貴是充滿樂觀精神的一個人,所以才能歷經各種苦難挺下來,黃渤將這種最重要的樂觀精神表現得淋漓盡致,而且他表演得很辛苦,高強度的演出安排和極繁重的主角戲份對于體力要求很高,接下去還要演10多天,說實話,這不是人干的活兒!飾演家珍的袁泉表演也很精彩,因為表現性格容易,表現內心很難。
確實,觀眾難免會對小說和舞臺劇進行比較。這次的編劇張先也是很成功的編劇,他曾經說過小說的成功程度越高改編的難度也就越大。但是這兩種藝術形式完全不同,我認為只要能夠把自己固有的形式發揮出來就是成功,沒有必要忠實原著。在我的心目中,只有自己心里沒有想法的導演才會忠于原著。孟京輝想怎么改都是好的,哪怕是改成《許三觀賣血記》也可以。我在倫敦看過一次音樂劇《悲慘世界》。看之前,我就很好奇這么大部頭的著作會被改成什么樣子。兩個多小時的演出,導演借用《悲慘故事》的故事進行再創作,把舞臺劇和音樂劇的形式結合并發揮,類似這樣成功的作品還有很多。
記者:我們了解到,您在今晚之前從未看過這部改編后的話劇,說不知道孟京輝會弄出什么東西來,但您第一次看完后哭了,這么多年后仍然很有感觸?
余華:《活著》這部小說解放前的段落是在北京寫完的,解放后的段落是回到嘉興寫的。如今已經過去了20年,我已經完全忘記了當時寫作時的感覺,但對于這部小說感受非常深。后來因為換了很多家出版社,校對重讀時曾淚流滿面。記得1998年去國外開朗誦會,要選段落——《活著》是比較悲傷的,《許三觀賣血記》是比較幽默的。第一站在維也納,我讀著讀著就哭了,翻譯也哭了,后來在瑞典朗誦時也哭了。一想到會掉眼淚,再開朗誦會我就堅決不愿意選《活著》。《兄弟》也是如此,我在寫的時候沒有特別強烈的感受,修改時痛哭流涕,邊上全是紙,因為幾萬字是幾個月慢慢寫完的,修改時則要一氣呵成。
(編輯:子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