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視野]詞來的春天:為香港文壇帶來突破——晚近香港流行歌詞及詞人
早在2004年,粵語流行曲教父黃霑已經說得坦白:“香港粵語流行曲死了。你必須知道一件事情,流行音樂是一個商品,1996年是19億,現在是3億,有些歌星的唱片出來賣幾百張,19億的生意變成3億就是死。”香港詞人其實不是沒有努力保持自我,在近年每況愈下的香港粵語流行樂壇中繼續艱苦作戰。突然幾年便過去,早已命懸一線的粵語流行曲雖然仍是艱苦經營下去,但以流行歌詞來說,卻是新人輩出,舊人作品亦屢見新意。現當代文學專家陳思和便曾指出,近年香港中文文壇出現“中年危機”,活力漸減,如將香港歌詞納入文學之中,或會為香港文壇帶來突破。
香港著名樂評人黃志華早年在名為《唱足四十年》的專欄中曾以南宋詩人鮑照《登黃鶴磯》中的“九派引滄流”論20世紀八十年代初的新詞人,我想這也適用于過去幾年間香港詞壇的新局面。“九派引滄流”上一句為“三崖隱丹磴”,其實也正好借來論述香港詞壇的三大掌門。《登黃鶴磯》情景蒼涼,與香港粵語流行曲給人的感覺或有雷同,但從另一角度看,詩人一生雖已流逝,但大江依舊川流不息,未嘗不是生命力的顯現。

朱耀偉
1965年生,現任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教授,人文學課程主任,主要研究范圍包括后殖民/全球化論述和香港流行文化。除了出版學術專著和學報論文外,也愛評論香港粵語流行歌詞,有關歌詞的近作包括《香港粵語流行歌詞研究I&II》、《香港歌詞八十談》(與黃志華合著)、《后九七香港流行歌詞研究》(與梁偉詩合著)、《詞家有道:香港十六詞人訪談錄》(與黃志華、梁偉詩合著)、《歲月如歌:詞話香港粵語流行曲》、《香港歌詞導賞》(與黃志華合著)、《詞中物:香港流行歌詞探賞》、《光輝歲月:香港流行樂隊組合研究》等。
三崖隱丹磴
幾代香港人實在不敢想象假如沒有林夕代他們談情說愛,內心情感如何可以說下去。其實對于曾經經歷香港流行歌詞的光輝歲月的歌迷而言,煥發紅光的遠山又豈止三崖?

香港紅磡體育館是香港流行音樂的殿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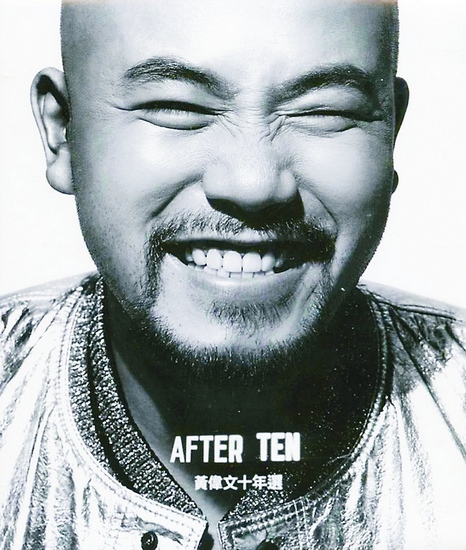

林夕、黃偉文、周耀輝是香港流行歌曲詞作的“三大掌門”
林夕的詞作大幅提升了香港流行歌詞的哲理高度。
誠如詞人喬靖夫所言:“這二十年來對香港影響最大的文人是林夕,無數香港人每天都用他所寫的文字來表達內心情緒。”幾代香港人實在不敢想象假如沒有林夕代他們談情說愛,內心情感如何可以說下去。過去幾年,林夕大幅減產,歌詞重點亦由談情轉為論道。借夕爺自己的話來說,他已經歷“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和“看山還是山”的境界。惟信禪師對門人說“參禪悟道,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個休歇處,依然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夕爺今個休歇處的詞作,如《弱水三千》的“山水非山水,凍了變雪堆,山水般山水,遇熱若霧水”便真的是“見水是水”了。《太陽照常升起》體現“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道理,“不來也不去”脫胎自《金剛經》的“八不”,《無念》說無念便是正念的佛偈,《夏花秋葉》寫出禪宗“如何是佛法大意?春來草自青。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的味道,都可見情感喑涌已化作云在青天水在瓶的感悟。林夕論道并不一定高深,如《你是哪種人》便以簡明的筆法,反問“出生怎影響出身”、“甚么種籽早種哪種人”,藉此帶出命運主題。既能深入亦可淺出,林夕的詞作大幅提升了香港流行歌詞的哲理高度。
見水是水的得道詞人,針砭時弊時卻不會手下留情,如《天水圍城》揭示香港資源分配不均,可見此人談情論道之余亦有盛世危言。林夕成功之處,在于不但可有理直說,亦能寓道于情。《一絲不掛》以《楞嚴經》的典故引伸出“絲”的不同意涵來說感情。從《弱水三千》到《一絲不掛》,可見詞人在語言和靜默之間可從容自若一絲不掛,又能像水那樣在不同情況以不同形態出現。《柳暗花明》是廣告主題曲,夕爺亦能聲東擊西以詞說道,借“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發揮,提醒我們“要跨過稻田,才明白我能拋開所有經驗,便遇上我也很向往的睡蓮”要是能夠放低習慣,便可走出露臺望見心花開遍。為學日益,為道日損,學習會令我們自困于習慣的框框,要是能夠離棄習慣,就會想到便能看見從來不能想象的東西:“柳暗加花明,何止眼前?”其實寫詞聽歌又何嘗不一樣?近年人們習慣了批評粵語流行曲情歌泛濫,水平下降,卻看不見詞人寫不同題材,說不同道理的嘗試。放下成見,用心聆聽,自會柳暗花明。
黃偉文近年與林夕一樣開始減產,但風格仍然繼續變化,詞中創意迭出之余更顯人生智慧。
過去十多年與林夕一起壟斷香港流行詞壇的黃偉文,近年與林夕一樣開始減產,但風格仍然繼續變化,詞中創意迭出之余更顯人生智慧。黃偉文曾說《浮夸》和《葡萄成熟時》是他創作生涯的高峰:“那兩首歌,對我來說,是一道很難跨越的墻。”《葡萄成熟時》以釀制酒過程比喻情感經歷,意象俗中見新。筆者曾經指出,最重要的是詞中既說愛情也顯智慧。詞人成功之處在于不是追求團圓結局,就算錯過了春天也不沉溺于廉價感傷,反而在過程中認清“將愛釀成醇酒,時機先至熟透”。假如葡萄比喻想要追求的理想愛情,紅酒卻不是等待的人,也非期盼的愛情,而是因愛情而來的智慧。黃偉文近年佳作證明他已跨越了他所說的那道“墻”,最佳明證是其詞作中閃現的人生智慧。以往會說“你當我是浮夸吧”,如今的黃偉文仍有時偏《重口味》愛《少數》,但叛逆創意中更多添一份細致淡雅。
《葡萄成熟時》是黃偉文著名的中年男人玩物系列的第一章,其后《沙龍》《人車志》和《陀飛輪》分別以相機、跑車和名表喻人生,情懷真的完全成熟了。黃偉文在其《Y100-That’s Y I’m Evil》精選碟中點評此歌時說:“這其實也是本人用‘你’作主角的新系列作品的最初回。此后‘你’的親戚還有《喜帖街》《小團圓》《那誰》等等。”從“世上萬物向心公轉,陪我為你沉淀”的自我中心情感漩渦,到《喜帖街》“你注定學會瀟灑”、《小團圓》“使你學會望闊點”和《那誰》“你那新生你也必須接受”的淡然優雅,渡日月穿山水后的詞人早在品嘗醇美佳釀。《落花流水》“淡淡交會過,各不留下印”已夠豁達。另一首作品《最好的……》談藝術說感情:“你不明白最動人的創造,永遠下場一樣,給糟蹋吧。”雖然很不忿,但“這些東西可做過的話,還是送他,很宿命吧,很宿命吧。”宿命在詞人筆下并不沉重,反而呈現出老莊的豁達:“完成了它,不惜一切代價,還清今世造化。”“人世茫茫,無常禍福,假若從未預告,唯有大方得體到底,我做到”——《黑色禮服》的優雅,在黃偉文近作中具體化為動人的人生智慧,換個角度來說未嘗不是另一種見水是水的境界。
周耀輝近年更積極融入主流,但作品仍不失獨特的另類想象。
兩個偉文(林夕原名梁偉文)近年作品數量減少,以往一向作品不多的周耀輝反而增產,在2011年CASH金帆音樂獎頒獎禮上更獲“個人最多新作品演出獎”,打破了兩個偉文的壟斷局面。他領獎時不忘自嘲說要好好檢討自己,因為他的作品一向給人另類的感覺,如今得獎難道表示其作品已不再另類?筆者一直覺得周耀輝擅于在主流和另類之間游走,近年他更積極融入主流,但作品仍不失獨特的另類想象。詞人在主流與邊緣之間的游走愈來愈精彩,真的像其文集所說的“十八變”。《黛玉笑了》般的作品玩味中國風重寫經典,《酷兒》一類詞作則續寫其性別想象。《也》是一個抹去了“亻”或“女”或“牜”的他、她、牠的文字試驗,《彳亍》更是又拆字又華麗,有著典型的周耀輝風格:“初生的我緩慢站起,彳亍走向十方,在我的無邊搜索,然后與歲月摔角,為了知生存過不生存過,很想在雨點崩裂時,去過,聽過,華麗與沮喪。”除了其簽名式寫法外,《彳亍》彳亍向前不斷搜索的精神,亦體現心境未有因為進入主流而不再年輕。叫人感動的是詞人凝融的不單是若水情感,也是主流和另類之間的天生隔閡。這正是周耀輝的魔力:主流但未落俗套,另類卻不失溫柔。
筆者曾說近年周耀輝的性別觸覺依舊敏銳,雌雄同體化身露西夏娃為男女歌手談情說愛,句句有如現代情感手冊;理論書寫仍然獨到,從愛上林夕的弗洛伊德到遷居長生殿的笛卡爾,篇篇仿似人文通識課本。移民阿姆斯特丹多年的周耀輝完成博士課程后,2011年初回港于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學課程任教,作品人文意識不減,更多添了一份在地情懷。《彌足珍貴》和《菜園屋村》都立足本土步入民間,前者在“孩子走過,一轉眼發現會漸老;時光淌過,街巷見證著故事老”的大千世界中尋找快樂,后者于“層層大廈拉下來”的萬變社會里“種下無邊的青春”,“將屋村變菜園”。以往我覺得假如要用一個詞形容周耀輝的作品,那應該是“華麗”。近年他的作品給人的感覺卻是既華麗也民間,簡單來說是變得快樂了,就像《快樂很我們》:“我還是快樂,就算哀傷太壯大,青春會消磨”。沒有沉溺于哀傷的華麗,只有簡樸的情懷。“民間”并非指他的文字風格,而是生活方式和人生態度。周耀輝詞作素來愛借意象、擅用感覺說話,簡單的“黃菊開了很多你,南風吹過很多我”,在黃菊前于南風中,就有青春有快樂有自我,言簡意賅。周耀輝以《快樂很我們》作為他在浸大人文學課程開設的歌詞創作班的畢業作品演唱會的開場曲,可見他不但保持年輕,還想以青春點燃下一代的創作火花,叫人明白如何可以年輕,怎樣能夠快樂。
其實對于曾經經歷香港流行歌詞的光輝歲月的歌迷而言,煥發紅光的遠山又豈止三崖?如陳少琪、劉卓輝、潘源良、張美賢、何秀萍等自成一格的資深詞人近年仍有作品,不過在日漸萎縮的香港唱片工業中創作空間不大,否則定能煥發更耀目的紅光。
(編輯:偉偉)




